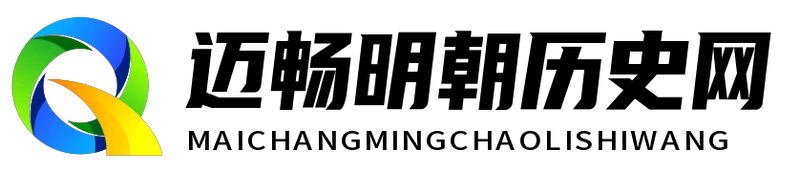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教育倡导的“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原则,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
智效民时期的大学

(作者:智效民,中国当代人文学者)
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接触到时期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青岛大学的杨振声,中正大学的胡先骕。这些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曾经被我们淡忘。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因此,要恢复教育的历史,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
一
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神权,提倡,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教育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这种理念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这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自工业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大潮。与此同时,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了洋务运动的衣钵,在很长时期内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偏颇和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重理轻文的观念和“批量性人才生产”的方式,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其是否合格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还可以原谅,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有意扭曲教育本质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做发财的手段。
除了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之外,大学校长还必须与官场划清界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事例。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另一篇说胡适多次出国是拿着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当年的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校长根本不是官,也没有被纳入官僚体系;第二,当年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完全不同,胡适不仅不可能拿学校的经费出国旅游,而且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还主动提出只拿车马费不拿薪水的要求。
既然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有良知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
二
因为时期的大学校长不是一个官,所以他们就只需要对学生负责而不需要对上级负责。所谓对学生负责,最重要的问题是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前面说过,由于学校像个工厂,这就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当年的大学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同上,第146-147页)对照这两段话,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
由此可见,所谓对学生负责,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为了一技之长而沦为“一只受过训练的狗”,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方面,学电机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做得最有效。
梅贻琦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着选》第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后来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因此, 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同上,第184-185页)
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风气之败坏”。(《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45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是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4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校体育馆发表演讲:“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还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着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同上,第334-337页)5月18日,他在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致答词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同上,第351页)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污吏的可能。9月18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371-372页)基于这一理念,他告诫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还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同上,第370页)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和竺可桢都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认为只重视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人格操守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要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大。因此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并想办法改变那些不正常的状况,才是对学生负责。
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它“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大学精神》第261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他认为:共和政体与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他指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写到这里,又想起前两年关于大学生道德滑坡的议论。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德育课如何重要,但该课程却始终处于“教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教育倡导的“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原则,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
标签: 中国历史简介表 、 明朝 生平事迹 、 历史朝代帝王列表 、 中国历史为什么只承认宋朝 、 大明王朝映射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