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世纪的英国,除了那些公有地之外,每一块土地早已有了自己的主人,为什么还能出现重新圈占土地的情况呢?说起来确实很让人奇怪,但发生在英国却是必然的。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在欧洲西北角的地带,即佛兰得尔地区,毛纺织业突然繁盛起来,在它附近的英国也被带动起来。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需求量逐渐增大,而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

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养羊的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需要而外,还要满足国外羊毛需求。这使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人开始投资养羊业。养羊需要大量土地,所以这些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农民赶走,他们甚至拆除农民家园,把可以养羊的地方圈占起来。一时间,在整个国家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成一块块草地,被赶出家园农民,则变成了无家可归流浪者。这就是著名的地主圈地运动。
当时,一位著名作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一本书《乌托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驯服且无欲,现在它们却变得贪婪和凶狠,以至于要吃掉人,它们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这个描述似乎颇为夸张,但对于那段历史来说,其实质是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经济巨大的变革。

圈地运动首先是在剥夺农民公共用地上进行。在英国虽然所有土地都已经拥有了主人,但森林、草原、沼泽以及荒野等公共区域则没有固定的所有权。一些强势贵族利用手中的力量,从这些公共区域开始扩展他们的手脚。当这些地方无法再满足日益增长的手头需求时,他们又采取各种手段将那些世代租赁自己土地的小规模农户驱逐出门村庄,并将周边所有可用的田产改造成牧场。
曾经有一群受害者通过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领主上诉书中写道:“这个权势高昂但缺乏正义感的人物——约翰·波米尔,用欺骗与暴力掠夺您的苦难臣民——我们过去承租他的牧场,这些都是我们家族继承下来的。他围起这片牧场,将其作为私有的领域。”

后来,这个约翰·波米尔又强行抢走我们的房屋及果园,有些房屋被烧毁,有些连房子也一起烧掉,我们被迫离开。如果有人不同意,他就派人包围住他的屋子,那些打手持刀剑或木棍,对他家的门扉进行攻击,不顾他妻儿悲痛哭泣的情景。而若有人拒绝,他会用一切方式包括监禁,让他们受尽折磨直至残废甚至死亡。此刻即便生命安全都不能保障!
为了适应不断增加对肉类制品供应所需,以及由于新的商品市场导致对其他产品更高需求,使得从事畜牧活动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商机之一,因此许多富裕的地主选择转型从事这一行业。然而,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获得更多用于放牧牲畜的大片领土,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拆除现存建筑物,如小屋、小仓库等;清理现有的耕作项目并推翻任何阻碍放牧路线的事物;最后,将失去使用价值或无法提供食物供给(如因恶劣天气条件)的地方全部封锁,以此确保只有最坚硬最健康动物才能生存下来并繁殖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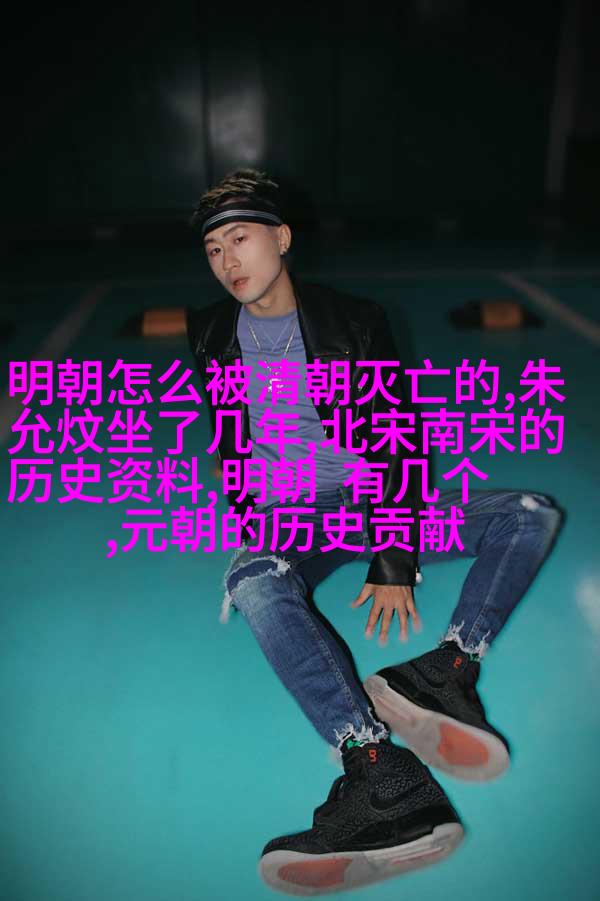
尽管如此,由于这种“狼性”般强悍无情竞争环境下只剩下最强壮健体型动物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快速繁殖,从而推动了整个人口结构由广泛分布在各乡镇之间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向集中化管理更大的企业迈进,大批普通百姓因为失去了赖以生计之源不得不流离失所,最终成为城市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对于那些试图逃离困境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但依然遭遇贫困挫折者的命运,也同样充斥着艰辛与悲剧:过度长时间工作、高额税收以及极低工资汇总导致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并可能面临加重惩罚(如鞭刑)、奴役状态或者甚至死刑判决作为惩罚措施。但为了避免进一步损害社会秩序并维护法律秩序,上述政策通常会严格执行以防止流浪者继续存在。
随着16世纪末期到18世纪初期,当局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同时考虑到了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因此决定采取行动限制流浪者的数量和行为。不过尽管这样做法令仍旧未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法律规定要求每个人必须定居于某个特定的地点,如果超过一定时间内没有找到合适工作就会受到处罚,而如果再次违反则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予惩罚,比如割去耳朵,或是终身奴役乃至死刑这样的极端措施频频实施以此作为震慑作用,以压制流浪人口增长速度和范围,同时鼓励游荡人员回到稳定职业岗位上任职以提升社会效率及稳定性,是一种既符合政府立法目的,又兼顾经济效益的手段策略应用计划。此举虽然有效缓解了短期内的问题,却进一步加剧了长远看待社会问题深层次根源影响力下的矛盾冲突激化程度使得该体系更加脆弱难以为久留,对未来构成潜在威胁,对现代观察者来说是一幅多方面复杂背景画面描绘出的历史过程跨越两个半千年的英伦风云变幻历程。

标签: 明朝 有几个 、 北宋南宋的历史资料 、 元朝的历史贡献 、 朱允炆坐了几年 、 明朝怎么被清朝灭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