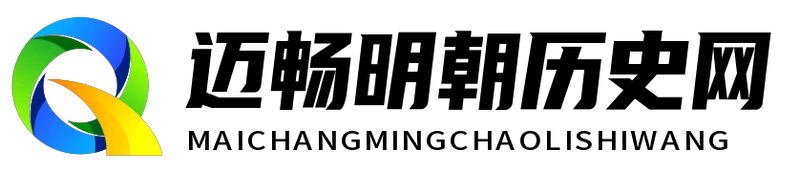在宋朝时期,有几个国家的文士们,爱不释手地蹭着各国的饭(图)。他们的心灵敏锐,其耻感比其他人强烈,大都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但那时候似乎例外,他们喜欢搞派对,喜欢去财主家去白吃白喝。去吃者雄赳赳气昂昂,放开肚皮大快朵颐,被吃者笑嘻嘻乐呵呵,扩大鼎锅大宴宾客,俨然是熙熙然共食的大同世界。

明宗室后裔朱承彩汗漫使钱,他家里有钱,却不私蓄,只隔三差五,就呼文士、引妓女到他家里去啜饮一顿。一年中秋,他搞了一回大派对,还邀请了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余士子鲸吸海饮,更喊来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佐酒助兴。
有金銮者,本来家里办喜宴娶媳妇的,不到家里坐上席,却到这里来蹭饭了。他说:“家里吃饭哪有蹭饭跟大家一起吃有味啊。”晚上通宵达旦摆流水席,千里宴棚能摆几日算几日。献歌的献歌、献舞的献舞、献诗的献诗、献画的献画。什么都不会的,就驴叫两声嚎两嗓子,“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

还有王伯稠这个人,他考过一次科举没中,从此打死也不去复读,只写诗只混迹酒局。他逢有派对,不管有无请柬下与他,他都带一张口,再带一副肚皮山吃海喝。他的朋友林春秀品行并不低下,也有一番诗名,但他常常不带分毫就到别人家去吃饭。他不唱个喏也不做首诗,最少也要唱个莲花落,这个王伯稠却是只管闷吃。
别人家的喜酒或寿礼,都没有他的热情,一上了桌,就是一个劲地食指大动,只听得见其喉咙里嘎嘎嘎,一上完桌筷子扔走了。这次那个“天外凤凰”应是自喻吧:“天外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椟鸣赤霄若奏钧天回举世那得见百鸟安敢猜。”

晚明也有许多这样的王伯稠,他们既不参加科举也不过问体制内讨生活,也不会顺着资产阶级萌芽下海事产业,或是在缙绅间游走,或奔趋于财主家的门庭入户,或写诗卖画赚几个小钱吆喝几个文朋诗友,有一餐好好享受,比如吴扩人品行并不低下但“以布衣游缙绅间衣冠白巾吐音如钟”,一点也不因为脸色难看刻意奉承财主与缙绅。
林春秀虽然自由撰稿也略知书法,但穷困潦倒,却爱死了喝酒,每日没得那酒就过不得怎么办?他就去了蹭酒喝,那个朋友郑铎天天给他送酒,一醉即狂骂人骂世连给他送酒的人也是骂个不断气还恕而且还特地给制作了一只杯子刻字云波,以为专用。而郑铎并非富翁,却仍旧如此慷慨无求谁能如此器量?

晚明那些时代里的文人们和资本主义初期商人的关系,是别朝所未有的融洽。当时已经开始出现商贾与士族之间互利共赢的情况,而这正是民间养士新风所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即便官府对于文人的态度冷淡,对于民间养士则保持一种默许甚至鼓励态度。
李渔常常带着全家的影子在各处打秋风向人要钱要物,无论面色多么苍白,我们往往讥笑他们其实,这可能正是晚明遗风的一种延续;清初另一大家金圣叹,在王斫山那里弄出千金银子的借款,说好了归还的事实上却挥霍殆尽,然后又抢白了别人的盛宴,“先生应诺甫越月已挥霍殆尽乃语斫山曰:‘此物在君家适增守财奴名吾已为君遣之矣’”。斫山竟是一笑置之,那些钱再大的数目,在当时被视作微不足道的事儿。这一切让我们想象,如果这些故事发生在其他朝代,它们将如何演变呢?

标签: 中国最富有的朝代排名 、 明朝的灭亡可惜吗 、 清朝12个 顺序 、 元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 明朝十六位 列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