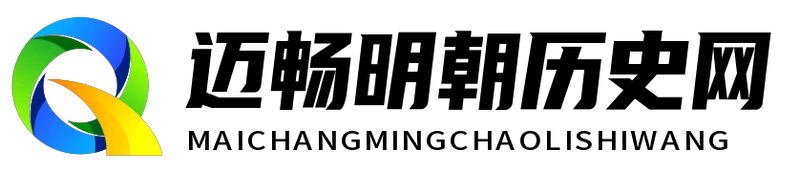由于袁自己也未必能分清“君宪”与帝制的区别,其形同的“君宪”被同样可能弄不清两者区别的时人普遍界定为“帝制复辟”并起而抗争,也就十分自然了。
黄克武北洋根本法的炮制与法统之争

(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一 制度建构:根本法的炮制与“法统”之争《临时约法》的制定与新旧约法之争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名义颁布《中华临时约法》,以取代此前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两相比较,《临时约法》最大的不同是将已经实施的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在之外复设“总理”是改制的标志。但《临时约法》规范的责任内阁制并不完备,要害在于改制之后未能确定府与孰为最高行政中枢。约法规定临时大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帅全国海陆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同时又规定“国务员辅佐临时大,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从条文上看,既然作为内阁长官的国务员只是“辅佐”,而被赋予“总揽政务”之权,则府应为最高行政中枢。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盖虽可“总揽政务”,国家的实际政务总是通过政府各部门来推进实施的,加之“副署”权的规定,也就赋予以巨大的权力。同盟会的一份通电亦承认:“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为责任之主体,所发布之法制、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在国务员之手。”[2]由于府和都被赋予相当的行政权,而《临时约法》又“并未说明内阁是对或是对议会承担责任”,于是导致一国之内同时具有两个行政中枢的政体格局。
将制改为内阁制并不符合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居正《辛亥札记》记载说,同盟会于1911年12月26日聚会孙中山寓居的上海哈同花园,开会讨论政府组织方案。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总理力持不可”。[3]居正提到的这次聚会,即“讨论制与内阁制之取舍”的同盟会“最部会议”。与会者除孙中山外,尚有黄兴、汪精卫、陈英士、宋教仁、马君武、居正、张静江等。孙中山在会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之大计。”[4]这次会议虽未能说服宋教仁放弃责任内阁制的主张,但同盟会核心领导层多数人的意见已经趋同。会后黄兴前往南京,同正在那里筹建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会商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12月29日,17省代表开会选举临时大,孙中山以16票当选,3天后宣誓就职。不久,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共和国政权得以诞生。
但孙中山的主张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13年春孙氏语涉政体的一次演说,暴露出其主张的前后矛盾,他说:“至于政府之组织,有制,有内阁制之分。法国则内阁制度,美国则制度。内阁若有不善之行为,人民可以推倒之,另行组织内阁。制度为担负责任,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美国之所以采取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以谋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为佳。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5]孙中山显然不至忘了自己不久前曾说过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此时却又说出这番话,可见其思想中的实用主义色彩。
将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带有限制袁世凯专权的明显意图,但这一举措犯了因人立法之忌。对此,深通法律的罗文干曾做过透辟分析,指出:“共和改创,孙不得不让位于袁以完成统一,而孙氏之党恐袁专擅,乃假手法约,设种种规定以束缚之,行政之权务求减削,立法之权事事扩张。袁本官僚,不知立宪,故元年参议院、二年国会初开,孙党(席位)多,大权既操之立法,而立法又多属己党,孙此时以为可以制袁之死命矣。吾人今日苟手南京约法,开卷一读,几皆属意见之条。”[6]《临时约法》另一重要制度性规定是通过立法来限制行政首脑的职权发挥。其显着特征在于赋予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在利用立法权来束缚行政权的时候,却没有想到立法部门的权力也应当有所制约。这集中表现在“同意权”的设置上。《临时约法》第33条规定,临时大有任命文武官员的权力,但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有此规定,本来属于行政方面的人事权也就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立法方面,但对与之对应的行政如何反过来制约立法没有任何具体规定。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所谓分权制衡是双向互动的。西方责任内阁制国家寻求立法行政制约之道,除规定议员可以对政府“动议指摘”,以及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迫使其倒阁或借以纠正其为政之弊外,大多同时规定行政首脑在必要时有依法解散国会的权力。《临时约法》只有“同意权”而无“解散权”,揆诸参议员之本意,大概是想操上之主动,制人而不受制于人。殊不知这种做法却因与其鼓吹的分权制衡理论不相吻合,不但不能收限制行政首脑之效,反而授人以柄,引起反对派的激烈反对,认为这样做不仅造成权力结构的“畸轻畸重”,在法理上难以成立,而且使政府丧失“独立机关之性质”,无以发挥应有的效能。
对于《临时约法》在政体规划上的缺陷,派中一些有识之士也有所认识。谭人凤就曾指出参议院被不适当地赋予“干涉军事计划之大权”,认为以参议员操持军务政务,正所谓“筑室谋道,安有成功之冀望”。一度比较激进的陈英士,在时过境迁以后写信给黄兴回顾失败的教训,也承认初建,以派为主体构成的参议院“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已多少悟出《临时约法》未能合理划分立法与行政权限的问题。曾经是队伍中一员的章太炎更是明确指出,临时政府建立后,在建设方面无能为力,了无建树。“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谋道,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因而提出尽快“改定约法”的建议。[7]由于各方大致形成这样的认知,修改《临时约法》,完善国家根本法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袁世凯担任临时大后,相关工作即展开。根据《临时约法》宪法由国会制定的规定,1913年4月8日国会正式召开后,便按照国会组织法,由两院各选30人为宪法起草委员,负责宪法起草。天坛被选作会场,起草工作历时三月。委员分属众派,意见歧出,争辩激烈,最后由国民、进步两党“调和公意”,完成全稿,因起草地为天坛,故称《天坛宪法草案》。起草期间,袁世凯曾向国会提出约法增修咨询案,试图解除国会对的束缚;国会议员以宪法草案正在起草,不必修订即将废除的临时约法,未予采纳。
从内容上看,《天坛宪草》较之《临时约法》有所改进,赋予行政首脑对于国会的解散权,如草案第75条规定“大以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与此对应,第43条则规定“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议决”,在法理上较临时约法更加完善。
王宠惠事后评论说:昔宪法起草委员会聚于天坛,成宪法草案113条。“此草案萃法学巨子于一堂,而经若干次之讨论始有此结果,洵可为吾国宪法史上放一异彩。”[8]但《天坛宪草》在对《临时约法》做出部分修改的同时,依然保留国会对于行政首脑任命官员的同意权,继续实施责任内阁制,与袁氏之意相忤,加之所提“约法增修咨询案”被国会否定,袁乃授意各省督军及民政长官出面反对,有谓宪法草案“比较《临时约法》弊害尤深”之语。
由于袁氏压迫,国会不久即放弃先定宪法、后选的原议,制定《大选举法》并“依法”选举袁为大。国会议员做此妥协,是想通过选举来缓和与袁的关系,以完成宪法的制定工作。然而,尽管多数宪议成员表现出对制度建设的执着,宪法草案全案也经过三读,初步完成了宪章条文的草拟和审议,却一直没能公布。以后,随着袁世凯解散国会,由两院议员组成的宪议消弭于无形,中华历史上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也随之流产。
不过袁世凯似乎并无根本否定宪政的打算。按照张绍曾的判断,袁世凯虽不满《临时约法》,但也认为国家不能无根本法,故解散国会后,便着手另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根本法。为此,袁组织了会议并由此衍生出约议,于1914年5月1日推出《中华约法》。该约法吸纳了袁提出的《临时约法增修案》并定有制宪程序,规定由参政院推举委员10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但不久帝制发生,制宪工作随之终止。[9]身与其事的张国淦曾将新旧约法做过仔细比较,认为新约法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恢复制,并部分取消了《临时约法》赋予国会对行政首脑的限制。一定程度上,新约法的制定有会议中“法律派”(如法制局局长施愚及顾鳌等人)的作用。该约法条文虽系彼等屈从袁之意旨而定,但既要经约议形式通过,法律派的意志也会有所表现。这主要体现在从法律的角度修正《临时约法》中他们认为有悖法理的部分,如立法单方面制约行政,以及有关人民权利的规定无“于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等。
袁世凯在推行帝制过程中,曾罗致包括杨度、严复等在内的主张君主立宪的学者为之鼓吹,也聘请包括美国宪法学家古德诺(F.J.Goodnow)在内的西人为其所为作符合国情的论证。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袁世凯希望实施的究竟是君主制还是立宪君主制?通常认为袁的中外顾问主张的是君主立宪而袁向往的则是君主,两者有本质区别。但何以主张君主的人要礼聘主张君宪的人作为自己的顾问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既有的解释是:由于古氏许多言论更倾向强调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而非立宪君主制与君主制的区别,所以很容易让帝制派偷梁换柱,在君主制名义下以君主制替换立宪君主制。就事实而言,袁最终实施的帝制显然更加有类前者而不是后者。但即便接受这样的解释,袁究竟是热衷封建帝制复辟,还是因不能区分立宪君主制与君主制,并在试图效法克林威尔和拿破仑在非常时期以非常手段集权行政的冲动下将君主立宪做成了畸形,也还需要认真论证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涉及不同政体的辨析。梁启超认为,辨析政体属性的关键不在君主还是共和()而在立宪。在这一问题上,如果大多数可以视作袁统治的社会基础和支撑的人都主张立宪,袁为何偏偏要与他们在上大异其趣呢?或许袁弥留之际回答徐世昌如何接办其身后事之垂询时仅说出的两个字可以回答这一问题,这两个字是“约法”。[10]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临时约法》及约法上一切机关均行恢复。鉴于《临时约法》毕竟非同宪法,殆国会重开,乃权衡利弊,接受《天坛宪法草案》,继续其未竟事业,制定根本法。因《天坛宪草》系仓促成篇,对最有争议的地方政制问题未遑议及,故国会审议草案,便有议员提出有关地方制度的意见。但辩争激烈,未有结果。再往后,因对德宣战问题,政潮大起,督军团压迫国会不成,恼羞成怒,借口宪法已议决,各条不合国情,要求解散国会,遭黎元洪拒绝。各督军遂纷纷举兵,以至张勋进京,拥清帝复辟,解散国会,制宪又成画饼。
第二届国会,并选出委员起草宪法,于1919年8月将草案议决。草案内容与《天坛宪草》相似,无须具论。
但段的举措却导致了新旧国会之争和持续数年的“毁法”与“”冲突,酿成战乱。对于孙中山领导的运动,既有研究大多予以正面评价,但时人杨荫杭的认知则有所不同,他指出:“因北方武人破坏法律,于是乎有‘’,用意至善也。然频年,频年内乱,人民怨讟,信用丧失于外,而法律破坏如故,北方武人之跋扈如故,则知所谓者,实未尝有丝毫之成绩。虽爱者,亦不能为者讳也。
不但此也,广西人,广东人亦。同是也,何以一转瞬间,广西人与广东人又互相吞噬,一若有不共戴天之仇?向者与北方不能相容,固曰法律破坏,广西人与广东人不能不合力以护之也。试问今之所护,又是何物?
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产生及夭折1920年夏,皖系为直系,由安福系操纵第二届国会完成的宪法草案自然不被尊重。1922年6月,直系打到奉系,“法统重光”,1917年去职的黎元洪复职,被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再度恢复,但国会制宪并不顺利。其间国会有减少法定出席人数避免流会以促成制宪之议,因府院之间屡起纷争,直至黎离职,直系控制局面,政潮趋平,方致力于制宪,将1917年悬而未决各原案及修正案重付审议,并将审议结果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此番制定的宪法共13章、141条,其与此前两稿宪草不同之处,主要是“国权”与“地方制度”两章。“国权”一章列举中央与各省各自权限若干条,其未经列举事项,性质关系国家者属之国家,关系各省者属之各省。“地方制度”一章将地方分为省县二级,省得自主制定省宪,惟制宪机关之构成由国宪规定。此外,民元以来争持不休的同意权与解散权的关系问题,也以共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1923年10月10日,宪法全案由宪议公布。于是,从1913年天坛起草,经1916年、1917年的论争,再经南方时代重新审议,整个制宪工作至此总算告成。从法制史的角度观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价值和意义非同寻常。
不过宪法虽经制定公布,却又产生了合法性的争论并直接影响了这部宪法的命运。曹锟当选及制宪过程中,因议员南下者甚多,难以达到法定开会人数,为吸引议员赴会,曾发给500元出席费,后又填发面值5000元的支票,待投票结果出来后兑现。这5000元的支票,被视为曹锟贿选的“千古铁证”,众议员邵瑞彭据此向检察机关提起控告。种种迹象表明,曹锟谋当期间,确有重大行贿嫌疑。但要在法律上认定为“贿选”,将授受双方按刑律论处,需要考虑的因素尚多。根据议院法,众议员是应领取薪俸的,标准为岁费5000元。但因国会时开时停,加之政府财政困难,议员薪俸,“减成发给,至多月份未有过三百廿元者”。至欠薪总数,据国会方面统计,“政府积欠民二、民六及民十一岁费旅费等项,每人应得4600余元”。
议员因生活困难,多次索饷,至有要求吴景濂“辞职让贤,勿尸首席”者,对政府造成巨大压力。直系方面此时开出5000元支票,是否有补发欠薪以示好议员的考虑?这显然是应该纳入思考范围的问题。从程序上讲,据有关资料记载,支票发出之前曾“疏通异党”,并“邀集三十六政团”讨论支款额度,“经两旬期间之切实协商”,确定为5000元。虽然各方如何协商的具体材料未见其详,但揆诸常理,行贿这种有违道德的行为是不会通过协商方式(特别是与异党沟通方式)决定的。反过来说,既系各方协商决定,就很难认定只是曹锟及其统领的直系一方在“贿选”,但如果认定系各方共同“贿选”,则其他方面又未必有行贿的主观动机。
一些官方文件曾涉及经费支出的性质。蒋雁行在给曹锟的密电中透露,为联络南下议员回京,政府曾许以“回京费二百、三百、四百及多数五百元者不等……此间之出席薪费,仍旧照发,以全面子;并各给以五百元之川资,即可北上,决无问题……据佩绅在沪所得信息,奉省筹60万,浙省20万,以40万给参议院,以40万补发在沪人员正费”。[12]从密电中可以清楚看出,所支经费的名目是“薪费”、“川资”及补发南下议员的“正费”。
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名目下支付,所以接受支票的议员大多能安然受之。曾经接受5000元支票的议员汪建刚就明确表示,自己“虽然接受了众议院会议科所送补发的岁费五千元,但并未附带什么条件,也没有在选票上写过曹锟的名字,自认为比较干净,常常向人撇清”。[13]汪氏在这里强调了两点:一是接受的款项系“众议院会议科所送补发的岁费”,二是付款“并未附带什么条件”。关于前一点,反直人士一直将其说成是“票价”,但汪氏则强调他接受的是“补发的岁费”。这虽然带有自我辩解的成分,但欠薪是事实,在欠薪的前提下议员将直系所开支票理解成“补发的岁费”,应该说得过去。身与其事的陈垣30年后检讨往事,亦称曹锟系“利用补发欠薪的名义,凡参与选举者就在出席时交给你五千元支票一张”;既系“补发欠薪,受之何愧”,故陈接受了支票。[14]虽然当时官方文件中未见“补发岁费”的正式提法,但蒋雁行给曹锟的密电罗列的支款名目间接透露了支款的补欠性质。而有无附加条件对于判断支票性质更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吴景濂曾发表可以“出席不选曹”的谈话;对此前曾“拆台”后又出席的议员,亦曾有“投票自出,票价照付”的承诺,足证汪氏无附加条件的说法。
汪氏强调的两点应为判断曹锟是否贿赂议员以求当选的关键。因属“补发岁费”,且无附加条件,故汪能问心无愧地接受支票,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不投曹锟的票。此外,还有一部分议员,以为曹氏既无袁、段之凶,亦无袁、段之才,将其推为,或有利于国会实施对政府的监督,并借此完成制宪,将国家带入宪政轨道,故投票支持曹锟,其投票与接受支票并不发生直接联系。
曹锟是在直系与反直各方斗争的大背景下谋当的。当是之时,双方斗争异常激烈,手段亦无所不用其极。以北京国会多次开会未达法定人数的原因为例,姚震在致奉方重要人物杨宇霆的信中坦承:“北京三次开会未成,皆我方设计破坏”使然;又称“直方选举,经我方极力破坏,三月以来,各会皆未成立”。反直各方破坏北京国会开会的手段是出钱收买议员。“安福系公然在京收买不出席议员”,奉方收买议员开出的价码“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对南下议员的“岁费”和“从前欠发的岁费”,奉方亦全力筹发。大选“拆台费”仅浙卢方面就提供了300万,出现了与“贿选”相对应的“贿不选”行径。就是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提供支票作为“贿选”证据的反直议员邵瑞彭,因支票并未作废,也从李思浩那里以“借支”的方式兑现了5000元,一举两得,名利双收。反直各方攻击曹锟“贿选”,其实严格地说,反对派的“贿不选”才是真正的行贿,因为津沪方面虽汇聚了部分国会议员,但数量远不够法定人数,且国会机关及国家行政中枢不在津沪,反对派连给议员发放“岁费”的资格都没有。反直各方如此动作,迫使直方以牙还牙,以非常手段加以应付。更有甚者,进行议会斗争的同时,双方都秣马厉兵,做军事上打垮对方的准备。吴佩孚就明确提出了以“选费作战费”的设想,张作霖、卢永祥亦紧张备战。可见双方的斗争已经超出合法的议会斗争范畴。
既然争的是,单纯从法律立场来思考问题,也就难得要领。即便退一步言法律,由于有关“贿选”的指控主要是曹、吴的政敌提出,一些关键性的证据也是与直系对着干的人所提供,真假难辨,定谳难度极大。
从国会构成来看,除了直系议员之外,反对派议员亦复不少,而支票发放对象是所有出席议员,且候选人不止曹锟一人,如果说发放支票是在“贿选”曹锟,岂不意味着同时也在“贿选”他人且“贿不选”曹锟?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综合上述因素,直系在选举前夕给议员开具支票的做法不能说没有行贿嫌疑,然而在欠薪的前提下通过各方协商公开发放支票以示好议员与秘不示人的行贿毕竟有所区别,在找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切实证据证明其确属“贿选”之前,暂将其定性为通过兑现某种承诺以寻求支持的不规范的行为似乎更加妥帖。
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此举被反对派及普遍解读为“贿选”,并因此引发各地汹涌的反贿选风潮、奉系联络粤孙与浙卢倒直的战争及否定议会制度的。虽然也有相对平和的主张,如张君劢就提议,对于曹锟当选,可“以国民投票的形式承认之”,并得到江苏国会议员凌鸿寿的响应,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当是之时,激进派明显占据上风,激进人士甚至以“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为由,否定其视为“猪仔”的议员制定的宪法。本来从文本角度看,这一宪法对此前的约法及宪法草案做了诸多修改,避免了此前根本法的某些缺陷,不无可取之处。但“十年来苦心争持的宪法,竟在这样的时机和环境的里头宣布,真是宪法的大大不幸!这种宪法在当时有实权的人眼中完全等于废纸,那更不用说了”。[15]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随着曹锟政权被推倒,宪法随之废弃,在中国仅断断续续实践了不到十年的国会制度,也因议员贿选的指控而成为牺牲品。
曹、吴倒后,段祺瑞主政,不认从前一切根本法,提倡善后会议处理政局,以国民会议改造。在段主持下,善后会议制定国民代表会议规则,根据这个规则,组成了国宪起草委员会。到1925年12月,又草成一个《中华宪法案》。这个宪法案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宪政运动的最后一幕,亦为民初宪法草案的最后一篇。[16]时人对民初制宪经验的分析总结综观民初及北洋时期宪政史可以看到,《临时约法》制定之后,中国便形成“”与“毁法造法”竞争的格局。关于该约法与民初政局的关系,鲍明钤在《中国民治主义》一书中指出:“当国家从绝对转为共和,缺乏议会的实践经验和程序,立法机构便立即获得了任命总理、内阁部长、大使等的同意权,这给议会干涉国家行政以众多机会。”鲍氏认为,《临时约法》这一缺陷,“使中国付出了内战的沉痛代价”。[17]事实也正是如此。《临时约法》付诸实施后,派控制的立法部门与袁的行政部门冲突不断,终至发生二次。以后,几乎每次制宪,都有战争发生:袁世凯炮制“袁记约法”并公然称帝,引发了护国战争;袁死后黎元洪继位,恢复民元约法,又因宣战问题府院争持不下,张勋拥清帝复辟,导致段氏马厂誓师起兵动武;孙中山在南方建立非常国会及军政府之后,又有牵动南北的“”与“毁法造法”之争,屡动干戈;逮至曹锟制宪,又触发推倒曹、吴的直奉战争。整个北洋时期的制宪,可以说无一不与战争发生联系,以至时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宪法为不祥之物,其得之也,必先以杀人流血于前,其失之也,亦必继以杀人流血于后。
不过民初的乱源主要并不在主导制定《临时约法》的党人。党人鲁莽灭裂,固然要对当时的动荡负一定责任,但其主观愿望是要使中国朝着他们理解的“共和”方向发展,尽管其所作所为能否将中国导向这一方向尚有疑问,但袁世凯却是要将中国发展引至标榜“立宪”的君主制方向。本来,推翻清朝统治之初,“君宪”未尝不可作为中国政制的一个选项,但在“共和”制度业已建立的前提下再行“君宪”也就意味着改制,而改制必然伴随的利益调整能否为各方接受显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此外,由于袁自己也未必能分清“君宪”与帝制的区别,其形同的“君宪”被同样可能弄不清两者区别的时人普遍界定为“帝制复辟”并起而抗争,也就十分自然了。
然而民初及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此,而在或一派制宪,缺乏广泛的代表性,顾及了党派的得失却不甚顾及国家利益,将约法或宪法做成了维护特定党派利益的制度规范,做成了因一人或一时而定的“根本法”。王宠惠曾针对民初根本法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宪法之制定,有二要义焉:一曰,宪法者非因一人而定,乃因一国而定也。二曰,宪法者非因一时而定,乃因永久而定也。”“宪法必依一国之恒态而定,不能依一时之特别事故而定。此特别事故,倏然而兴,亦溘然而灭。若不惜以一国宪法殉之,其结果将变更时起,国无宁日。”[19]很明显,民初及北洋时期的根本法制定均未遵守这样的原则。
此外,根本法未规定现役军人不得任,亦是制宪的重大缺陷。曹锟谋当并极力推进选举之时,议员彭养光曾通电宣告其“罪状”,其中一条是:“军人非免役六月后,不得为选举之竞争,欧美先例,限制綦严。锟手握重兵,何求不得,将来帝王,为所欲为。”[20]但彭的指责在当时的中国并无法律依据,因作为宪法重要组成部分的选举法并无这样的限制。梁启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曹锟谋当期间,曾致函劝其不争,且倡行天下,“主宪法上规定现役军人不能当选”,[21]以提倡文治,但未被采纳。问题在于,不仅曹锟时代,整个北洋时期所制定的根本法,无论是约法还是宪法,也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均无此规定。尚且可以现役军人担任,地方行政由手握重兵的实力派操控,也就不可避免。
通常认为《临时约法》体现了近代精神而袁记约法则处处为集权张本。毋庸讳言,袁记约法浸润着很强的集权行政首脑的意识,但袁氏炮制新约法,从技术角度分析,只是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罢了。在这一问题的认知上,罗文干的分析或可供参考,他写道:新约法内容,一言以蔽之,袁氏为己之约法也。其病与南京约法同。南京约法困袁,新约法便袁,皆非为国为民之约法也。故南京约法行政之权唯恐其大,新约法行政之权唯恐其小;南京约法立法之权唯恐不伸张,新约法唯恐不缩小。于是内阁制改而为制矣,议员得指派矣,选举得指定矣;此走一极端,彼走一极端,前者出于私,后者亦出于私,所谓力者是也。[22]《临时约法》是同盟会议员主导炮制的,然而,不仅与同盟会处于竞争状态的人批评其不成熟,就是孙中山也对之不满,他曾说过,在南京所订约法,内中只有“中华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他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负这个责任”。[23]孙中山之所以拥护这个他自己都不满意的约法,是因为该约法将适用于袁世凯就任大之时,派普遍认为可以用来束缚袁的手脚。殊不知这样做与袁世凯炮制新约法一样,都将根本法做成了适用一人一事一时的制度规定。既然不是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来规划根本制度,人存政存、人亡政息也就不可避免。到了1920年代中期,国家根本法建设的规范化问题仍然悬置。罗文干认为,今后制定宪法欲免再蹈覆辙,必须同时具备三大要素:非为一人一时制定;合于国家的历史、国情、人心及风俗;有制裁力,非装饰品。[24]罗氏所言,可谓民初及北洋时期制宪活动经验的最好总结。
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卷》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