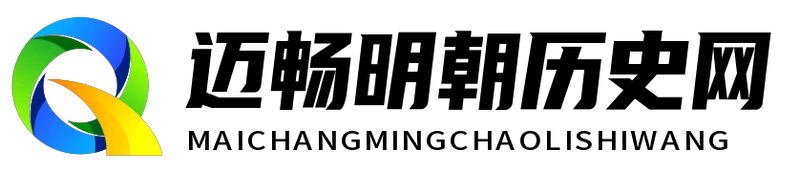统治权在城市中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因为工会与农会合作,如是一省中形成两种对峙的统治权——工农的统治权和所谓省政府的统治权。
黄克武农运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

(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无论是沈定一,还是彭湃,他们最初在各自家乡开展农动时,充分利用其在地方社会的精英身份、家庭地位,以及熟人社会的人脉关系和人际网络。不少学者发现,初期,各地者均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每个人在其家乡熟人社会的圈子毕竟是有限的,的范围一旦扩大,熟人社会的圈子势必被突破。从理论上讲,熟人又有熟人,可以一波一波地不断扩大和不断复制,但当群众运动需要于短时间内在一省或数省范围内大规模展开的时候,这样一种熟人网络模式显然太过缓慢。彭湃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海丰发动农动的过程中,最感需要的是从事农运的人才,因而当他出任中央农民部秘书后,即建议首先创办农动讲习所,“大批量”培养农运人才。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其效率将大大超过个体的熟人网络模式。学员在讲习所经过短期培训后,部分被任命为中央农运特派员,部分分遣回原籍开展农运。这看似复制彭湃模式,但从这些农运特派员的下乡经历来看,他们回到本籍所在县以后,除了他自己所在的村庄有熟人关系可以利用外,对县内的大部分乡村其实都是陌生的。那时一个县的范围相当大(1949年以后很多县被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交通条件又极差,人际交往范围非常有限。
他们在一县之内宣传和调查时,其实很少有人脉关系可资利用。有时乡土关系也可能形成阻力。如一位农运特派员在自己家乡开展农运时,反而遭到本宗族头面人物的责骂和殴打,“并行其家族主义”,以将其“出族”相威胁。
另一方面,农讲所学员大多资历甚低。据广州农讲所章程,学员入学资格如下:“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身体强壮,勤敏忠实,无恶劣嗜好,在中学毕业及有相当之程度者,始能合格。第二、三届不限中学卒业,凡农民协会会员,或佃农子弟均一律录取,并声明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38]第一届学员,中学毕业者居多,还算得上“半知识分子”。第二届以后,学生的比例减少,农工的比例大增。第三届128名学员中,佃农72人,自耕农20人,乡村学生29人,工人4人,小商人1人,军人2人。农民占到72%。即使是学生,也“取材于纯粹农民子弟”,明确声明“不收田主及绅士的子弟”。
农讲所学员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和个人资历,受训回乡后,其实很难赢得当地农民的信仰。在乡土社会,地方精英的身份地位,绝对建立在家庭经济及个人学识道德基础之上。同样是贫苦农民,他们一致信仰当地有名望的绅士,而相互之间则未必瞧得起。一位亲身经历者忆述:“当时我们动员的对象是长工、使女、女工以及肩挑小贩和贫苦渔民、船夫和靠打柴为生的等。可是这些人之中,有的很多顾虑,一般要看当地有信誉的农民的行动以为转移,因此乡农协成立以后,所选任的委员长,多半是农民中有地位的人,真正的贫雇农不多。”
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吊诡。站在的阶级立场,农动必须以底层的贫雇农为中心,然而,真正的贫雇农无法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仰。贫雇农之间也相互轻视。早期中团员多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沈定一、彭湃开展农动时,正是利用其家庭地位、个人资历以及与当地上层精英的关系。他们在当地社会的人脉和影响力,是“纯粹农家子弟”出身的农运特派员望尘莫及的,也是无法复制的。
虽然如此,农运特派员在1920年代的农动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农运特派员虽然不具有沈定一和彭湃那样的乡土社会地位和人脉,但他们或由中央委派,或由省党部委派,正是借助中央或省党部的权威,以特派员的身份为护符,不仅对普通农民具有相当的权威和号召力,也使地方当局和豪绅有所畏惧和顾忌。广东区委就批评农运特派员“时常拿上司的面孔去对付农民,把自己变成衙门委员一个样子”。“过于依靠力量工作”,“以为省农会的特派员是同县公署的委员一样”。广东区委还提到,农运特派员“往往到农村做工不几天,就要讨老婆”。而讨老婆要300元才办得到,而特派员每月的生活费不过30元,于是接受农友的“礼物”,实际等于受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农友为什么会给特派员送“礼物”,显然是特派员具有相当的权势。既然特派员自视与衙门委员和县公署委员一样,那农民眼中的特派员更是如此。农运特派员既可利用其权力寻租,自然也便于开展农动。乡下农民对城里人,本来就怀有几分敬畏心,更不必说来自省城有特派员头衔的“衙门委员”了。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陈炯明的亲属派了许多弁兵到乡间收租,该乡因为遭了大水大风的灾,农民没有租给他们,去的兵士本是海丰人,当即说广州话去吓农民,农民很恐慌,相率逃避。”说省城话也能吓唬农民,颇见当时农民对城市人的畏惧心态。对特派员来说,这样一种畏惧,既有可能成为受农民排斥的因素,也有可能成为令农民敬重的契机。从农运特派员向中央农民部的报告看,更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在农运过程中,农运特派员有时会通过与中央或省当局的关系,寻求支援。如广东农运的几次大规模冲突中,农运特派员请求广州中央派军队援助农民,得到广州中央的应允出兵。农运特派员请政府出兵时,“在报告中说了许多许多的如何危险的话,催促政府赶快出兵。此时中央农民部,天天都有接有我们的报告”。农民看见特派员能搬来政府军,自然对特派员更加信任。
在湖南耒阳,曾组织百余人分派九个“农运指导团”下乡。有一位指导团成员在报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他们来到该县石嘴乡,发现“该地的群众有多半在土豪劣绅手里,因为以前县农协有一特派员,不明当地情形,对于民众贫农及失业农民,稍微打击了一下,因此民众不敢起来,领导权就被他们拿去了。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不客气的打击土豪劣绅,促使以前被打击的的农友——贫农及失业农民【干起来】,于是反的土豪劣绅也就逃之夭夭,的空气也就膨胀起来了。”这一案例说明,农运如何因特派员、指导员的干预而起伏。
特派员下乡发动农动时,一般都擅长“造势”,如成立区、乡农民协会时,召开隆重的开幕式,让地方党政机关与各团体派代表参加,参会人数有时多达一两千人,会上,自己代表中央或省党部授旗授印,发表演讲,会后组织群众性,高呼口号等,从而在民众中扩大农民协会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广东团委在指导农动工作时,特意提示说:“农民协会之关防及布告,应比官厅宏伟辉煌,令农民易于注意,而暗中形成一无产阶级未来之新国家——政府。”这是利用农民对官厅的敬畏心理,提升农民协会的地位。
农动讲习所与特派员机制,可以说是大时期开展群众运动的一大创制。特派员的正式身份虽然是中央农民部或各省党部所委派,其实绝大多数特派员是中员,实际受的领导。如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提到,“现在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湖南区委的报告也提到,湖南省党部派出的农运工作人员,约百分之九十是本党同志。
按理在控制的省区,完全可以通过行政系统或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建立农民协会。而一开始即有意撇开既有的行政权力系统,让以特派员的身份直接深入乡村基层,然后自下而上建立农协组织,另立一套组织系统来动员群众。在湖南,先后派出的农运特派员多达400余人。而湖南的农运也最为活跃,最终导致各级农协组织几乎取代了省以下的政权系统。据柳直荀描述,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湖南实际已形成“工农”的局面,“城市中的工会,乡村中的农民协会,简直是当时第二政府”。
统治权在城市中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因为工会与农会合作,如是一省中形成两种对峙的统治权——工农的统治权和所谓省政府的统治权。但省政府的统治权仅是达到省政府所辖的各机关,而各机关并没有能力去执行政务,一定要由省政府函请工农通告各级工农会才能发生效力。
特派员机制,本是尚未掌握政权情况下的一种群众动员机制,而后的多次群众运动中,以“工作队”的形式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不同的是,此时根据地政权系统已掌控在之手,却仍然撇开常规行政体系,另派“工作队”来运动群众,其利弊得失有待深入探讨。
更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卷》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
标签: 历史真实的孝庄 、 历史真实的孝庄和多尔衮 、 明朝那些事儿9本和7本的区别 、 宋朝 顺序列表关系图 、 元朝16位 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