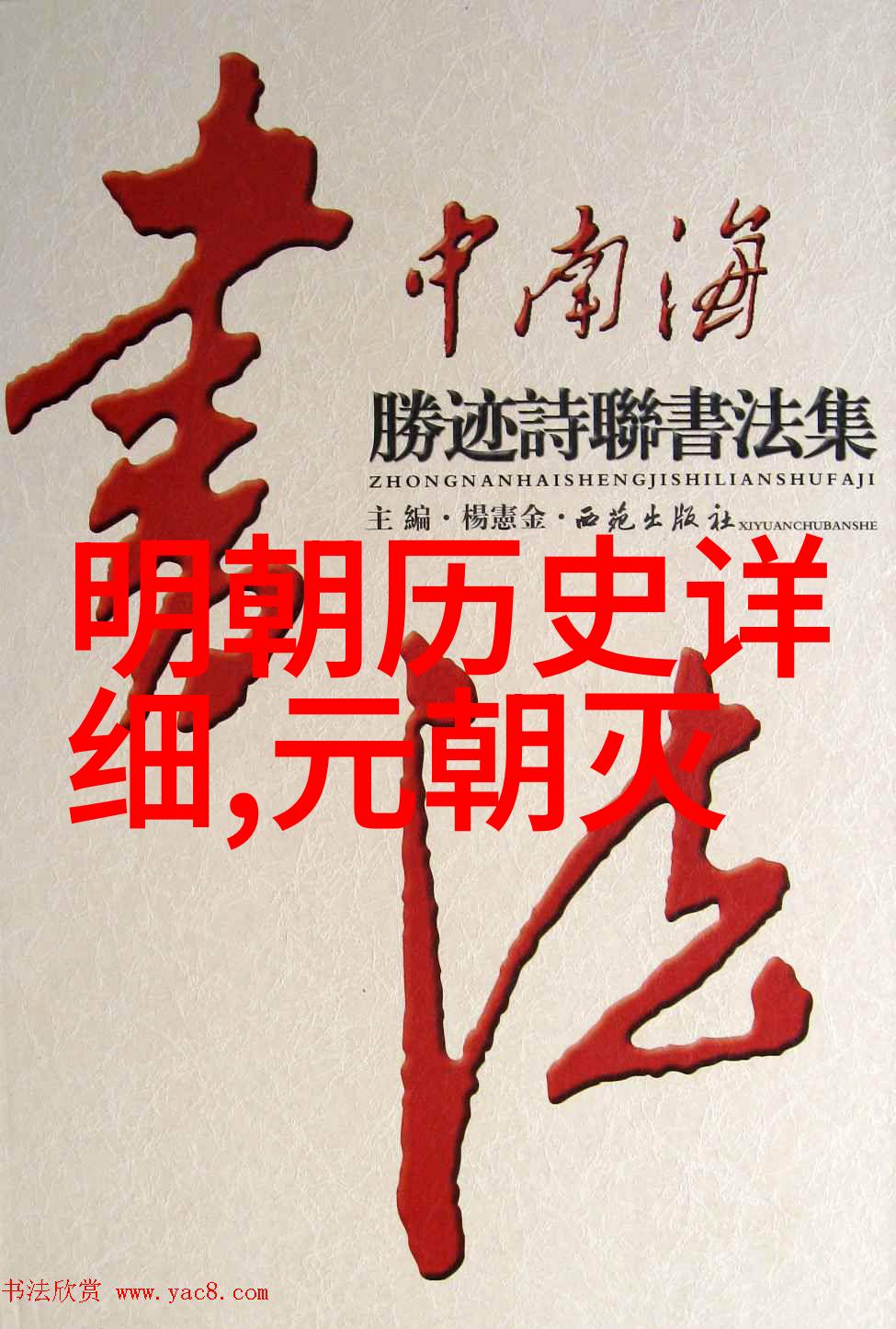在春节期间,一则关于傅向东团队发现赤霉素信号传导新机制提高水稻氮肥利用效率的新闻被淹没在疫情防控的信息海洋中。这一新发现虽然引起了业内关注,但并未成为焦点。然而,这一研究成果深化了对植物赤霉素信号传导和氮素响应之间复杂相互作用机制的理解,是傅向东十多年来对植物生长发育机制研究的又一重磅。

“创新为民,惠泽五州”,在傅向东办公室里,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题字醒目。这正是傅向东初心和快乐源泉。“能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国家需求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幸福的事。” 傅向东说。
他对遗传学产生兴趣是在高中生物课上。当时,他最喜欢做的是通过一系列附加条件推导出父母血型的遗传题目。因此,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尽管有老师劝他考虑热门专业,但傅向东坚定选择了武汉大学生物系遗传学专业。他师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尼克哈伯德(Nicholas P. Harberd),专注于赤霉素调节植物生长发育机理研究。

上世纪60年代,以降低农作物株高、半矮化育种为特征的第一次“绿色”革命,使全球水稻和小麦产量翻番,解决温饱问题。科学家们早已发现赤霉素能够促进植物生长,但其具体调控机理不清楚,因此主要工作就是利用拟南芥模式植物来研究赤霉素调控机理。半个多世纪后,被打上“绿色”烙印的小麦让农学领域专家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半矮化农作物株高变矮使得它对化肥不敏感。”
在英国,傅向东用实验证明了“绿色”矮秆品种氮吸收能力降低这一事实。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构建带有‘绿色’矮秆基因和不带此基因的水稻近等基因系,对比了两者影响,并发现植株变矮后的氮素吸收能力确实下降。此外,与同样的分蘖数增加但每穗少粒的情况相反,“绿色”品种减少分蘖数也导致穗粒数量增加。

如何在现有施肥条件下提高每穗穗粒数?这成为萦绕着他的问题。他选择回国,不仅因为中科院条件不好,也因为这里是水稲功能基因组研究中心,而且研究所环境好,可以做些国家需要的事情。于是,他放弃继续探究赤霉素作用机理,而转而解码超级稻高产性状形成分子机理。
随着时间推移,他意识到,要想提高作物产量,同时解决环境问题,还必须重新思考当年的疑问。他带领团队找到与植物氮素吸收及利用率密切相关的GRF4基因,从分子水平揭示了“绿色”矾秆育种伴随氪肥利用效率降低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此基础上,他们找到了NGR5介导红色的信号传导途径调控水稼氪肥效率分子机制。

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与育种家合作,将基础研究与实践经验结合,以推动技术进步。他认为学生应该多思考,不要NO.2,更不要Me too;文要少而精,每个故事都要完整地讲述。在他的实验室里,有些2005年就开始做但仍未突破的事项,让学生郁闷。但他觉得,“一个东西只要你认准,就不要放弃”。 “只有走错一步才会走对下一步,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结果,那是工程不是科研。”
标签: 土木堡在现在哪里 、 元朝开始结束时间 、 明朝为什么短命 、 元朝版图 、 明末八旗军恐怖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