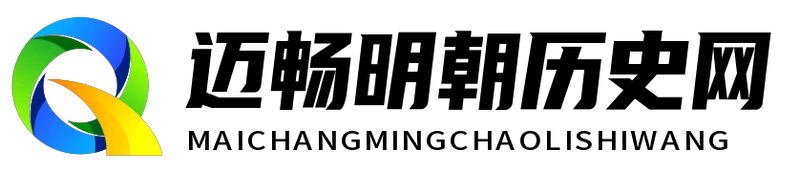淝水之战以后,东晋朝廷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在控制士族权臣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一时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出现转折。
孝武帝与皇权

淝水之战以后,东晋朝廷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在控制士族权臣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一时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出现转折。
东晋朝廷内部,士族当轴人物陆续凋零。桓冲死于淝水之战的第二年即太元九年(384年),于淝水战后未及受赏,于十年死。十三年,谢玄、谢石相继死。东晋士族人物,无论居中居外,无论事术,再没有过去那种人才相衔而出的优势了。
东晋门阀,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门户取而代之。王导死,琅邪王氏浸衰;庾翼死,颖川庾氏几灭;桓温死,陈郡谢氏代兴。凡此都是人物存亡影响士族门户地位升降之例。所以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宁重长弟而不特重诸子。王导兄弟辈几乎都居重任,庾亮死而弟庾冰、庾翼相继握权,桓温临死不以世子而以弟桓冲代领其众,继诸兄弟之后始出仕而又于宗门中特重其侄谢玄。这些都是士族慎择人物以图光大门第之例。庾翼临死,庾氏门户中才能出众的人已不可得,乃以子庾爰之代为荆州,引起满朝非议。何充表曰:“陶公(侃),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次子王恬。案导长子王悦先导死)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庾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案指庾爰之为荆州事)。”朝廷乃以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事见《世说新语·识鉴》“小庾临终”条注引《陶侃别传》。何充所举事实,特别是王、庾之例,客观上反映了当权士族以宗族门户地位为重,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择子侄之长而有能者继承权势,一般并不特重嫡嗣,因而何充得以引述这些事例来反对庾翼以兵权传子之事。从一个士族门户看来,有了其家族的地位,每个家庭的利益都有了保障。东晋门阀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当轴士族换了几家,但门阀的格局依旧。看来其原因之一,是士族重视宗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够从全族中慎择人才以保障门第。《颜氏家训·后娶》所谓“江左不讳庶孽”,我疑与这种社会情况颇有关系。东晋皇位兄终弟及较多,与此亦有若干相通之处。
南渡士族虽重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士族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感匮乏。南渡士族往往是在若干家士族的极小范围内通婚,尽管为了扩大通婚面而不拘行辈,“不讳庶孽”,也不可免于出现生理学上人才退化的趋势。东晋末年的政局中,各家士族都不再见到如前出现过的人才,这显示门阀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
门阀,以特殊际遇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局面。各家执政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这是秦汉以来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操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极少出现。但是从秦汉以来传统的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毕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长久维持。某些要求有所作为的皇帝,作过伸张皇权的努力,例如用近臣、用外戚、用宗室,以图抑制士族权臣。元帝曾用刘隗、刁协以制王导。明帝之初,起用庾亮以分王导之权,后来又用虞胤、司马宗等以制庾亮。但是当权士族对此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明帝所援引的外戚庾亮,本身就是门阀士族,他借外戚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庾氏门户势力,而没有真正伸张皇权。后来,以宗室近王而被援引入主中枢的司马昱,靠周旋于士族名士之间以自固结,成为玄学名士的保护人,所以能够得到士族的支持而长期居位。司马昱居中枢,与其说是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不如说是为了协调士族利益。他最后终于成为士族桓温的工具,屈辱而死。从这些事例看来,当士族尚有力量当道掌权的时候,伸张皇权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胜利者总是当权的士族。皇帝不能选择士族,而士族却可以按自己的门户利益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选择皇帝。即令是长君在位,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淝水战前的朝廷形势,太抵都是如此。
淝水战后,形势起了变化。谢玄北伐,值北方各族混乱异常,北府军胶着于中原,劳多功少;、谢玄面临皇权的挑战,步步退却,谢氏人物日就凋零;士族则既无勋劳又乏人物,不足以各树一帜,制约皇权。一句话,门阀士族已是今非昔比。另一方面,东晋朝廷经历了一个极度衰弱的阶段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努力,似有见成效的可能。
太元八年九月,当苻坚军已渡淮,正部署应敌之际,朝廷以孝武帝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与一起,参录机衡,司马道子地位得以提高①。淝水之战以后,功高不赏,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又以“谗谀之计”行于孝武帝与之间,遂成嫌隙,以至难于安居建康,不得不出镇广陵以避祸灾。据《晋书》卷八一《桓伊传》,孝武帝召桓伊宴,侍坐,桓伊抚筝而歌怨诗,词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闻歌,位下沾衿①。死,司马道子遂得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原来卫将军府文武,也悉数归入骠骑府了。
司马氏以相权辅佐皇权,发挥作用,暂时没有遇到来自士族的反抗,皇权在相当的程度上加强了。《晋书》卷九一《范弘之传》太元十六年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曰:“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宗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这种景象,可以说是东晋建国以来尚未有过。直到孝武帝末年,孝武对权臣防范还很严密。《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②,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刘惔)、子敬(王献之)比,最佳。’珣举谢混。”这表露了孝武帝对士族权臣的复杂心态:既不得不姻姬相联,又不得不防其僭越。
从孝武帝属王珣求女婿事中,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一,东晋末年的士族中,已找不到王敦、桓温那样才能出众、磊砢英多的人才;二,王珣是王导之孙,桓温同党,曾谓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孝武帝面对王珣指责王敦、桓温,意在表示对王、桓家族凌驾皇室的不满,借以警告王、桓家族;三,谢混风流有美誉,王珣虽与谢氏家族已成仇衅,仍不得不从人望以举谢混,可见门第与风流仍然是考察人物的主要标准,不过必须没有“好豫人家事”之嫌;四,谢混是之孙,谢琰之子,士族冠冕,影响尤深。他后来以党于刘毅而为刘裕所诛,而裕、毅相仇,主要就在于刘毅要结士族以自固。可见谢混一旦“小如意”,亦不免有“豫人家事”之嫌;五,在皇权加强的同时,士族既可能是皇权的障碍,又可能是皇权的助力。刘裕杀谢混,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谢氏对的影响;但是刘裕本人在受禅时,犹恨不得谢混以奉玺绂,使后生无从见其风流,说明皇权还是重视士族的助力。
皇权的伸张,既要排除士族超越皇权的可能,又要借重士族的社会影响以为皇权所用。因此,皇权承认并尊重士族的存在,只是要求他们从属于皇权。从属于皇权的士族,仍可居实权之位。太原王氏自不必说,如琅邪王珣,高平郗恢,陈郡殷仲堪等均以高名而任居内外,权势颇高。太学博士范弘之以言论件桓、谢,又不为王珣所容,不得不外出为余杭令。这是东晋末年的情况。入南朝后,皇权得到巩固,情况进一步变化,士族但居高位,享虚荣,难得再有实权了。就士族地位和皇权状况言之,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正是由东晋门阀向刘宋皇权的过渡。
前已述及,孝武帝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主要依靠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孝武皇后为太原王氏王蕴之女,王蕴及其亲属自然支持孝武帝。会稽王妃为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的从妹,王坦之的后人自然支持会稽王司马道子。太原王氏的这两部分,即王蕴父子和王国宝兄弟,均以皇室姻亲而成为东晋晚年政局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权势分别来自皇权和相权,分别从属于皇权和相权,也就是说,他们都从属于司马皇室,与前此居位的某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于是我们看到,以司马道子的相权辅佐孝武帝的皇权,加上主、相的分属太原王氏两支的后党、妃党的助力,东晋朝廷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门阀的格局。这种格局基本上与汉、晋以来以宗室、外戚辅佐皇帝、驾驭朝廷的格局相同,只不过有以太原王氏为代表的士族权宜维系于其间,还保留着门阀的痕迹。东晋政权在孝武帝时,如果不是司马皇室与诸家士族同样腐朽不堪的话,是有可能结束士族凌驾皇权这种门阀的格局,而回归于皇权的古老传统的。
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还可以从他用儒生、兴儒学这两端得到说明。《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范宁与邈皆为帝所任使,共辅朝廷之阙。”《世说新语·谗险》“孝武帝甚亲敬王国宝、王雅”条注引《晋安帝纪》曰:“〔王〕雅①之为侍中,孝武帝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见礼,至于亲信,莫及雅者。”范宁、徐邈、王雅等三人在士族中门第都不很高,都以儒学事孝武帝,与江左前此玄风流煽、名士纵横的情况大不一样。
范宁为范汪之子。范汪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范汪传》谓汪“善谈名理”,但这只是范汪干谒求进的一种手段。范汪一生行事,全在崇儒。《世说新语·排调》“范玄平在简文坐”条注引《范汪别传》,谓汪“通敏多识,博涉经籍,致誉于时”。他在东阳太守任内“大兴学校,甚有惠政”。他礼学精湛,《通典》载其议丧礼之文甚多。范宁更是“崇儒抑俗”,以为“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乃著论非之,比之于少正卯。范宁有《礼杂问》,载于《通典》中的范宁议礼之作,当系《礼杂问》的遗文。范宁的陈政事诸疏,类似汉代以来儒家论治道的常见作品。范宁先在余杭兴学校,养生徒,史谓“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后为豫章太守,奖学更力。《舆地纪胜》卷二六引章公弼《学记》,谓范宁于豫章大设庠序,远近至者数千人①,“自汉至晋旷数百年间,独得一范宁而已。”范宁有《春秋谷梁传集解》之作,序谓该书系范汪升平未免官居吴,率门生故吏、兄侄研讲敷陈而成,实际上可视为范氏家学著作。范宁子范泰也以博士起家,《宋书》卷六○《范泰传》记其议礼、兴学诸事,正是父祖流亚。范泰从兄范弘之,《晋书》入《儒林传》,颇有抑强臣、崇皇权的思想,因而不见容于士族诸门户。范泰子晔,出继范弘之,《宋书》卷六九《范晔传》亦谓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一生在名教中浮沉,卒至诛夷。自范汪至范晔四世,范氏是江左少有的一个儒学家族,而范氏兴儒事迹,多有见于晋孝武帝时者。
徐邈事在《晋书·儒林传》,曰:“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上。逸既东州儒素,太傅举以应选”,有《五经音训》之作,又有《春秋谷梁传注》,在范宁之后。逸子豁为博士。邈弟广除有《晋纪》外,还有《答礼问》之作,今《宋书·礼志》、《晋书·礼志》以及《通典》均有徐广议礼之文。
王雅为曹魏大儒王肃之后,居官“以干理著称”,似乎为学未杂染玄风。王雅后人王僧孺以《孝经》所论者忠孝二事,常愿读之。其人笃爱坟籍,也是经义文章之士,与玄学无缘。
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讲《孝经》,为一时盛事。《晋书》卷八三《车胤传》记其事曰:“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案此年孝武帝始十四岁,其时桓冲已让扬州,居位,讲《孝经》事当为筹划。《世说新语·言语》有孝武帝开讲之前“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胤)难苦问谢”之事,也说明这次讲经,主事者是兄弟。并于此年荐儒生徐邈为中书舍人,每被顾问,多所匡益。其人出入玄儒,居位以后以恭慎自持,企图恢复西晋初年以孝为治的气氛,表示输忠晋室①。这种振兴儒学的活动,与以后孝武帝伸张皇权的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另一表现,是企图恢复国学。案国子之学,成帝咸康时议恢复,但是如《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之言,“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国学就以军兴而废罢了。孝武帝太元元年,也就是孝武帝讲《孝经》的翌年,谢石又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学校之废,儒学之衰,时间已经很久,恢复起来也非一朝一夕可办。国子学如此,大学可知。至于地方之学,庾亮在武昌,曾下教兴学,并准临川、临贺二郡恢复学校的请求,但是均无成功。地方学校唯一可言的,还是太元时范宁在豫章兴学的成就,已见前叙。
总之,振兴皇权必与振兴儒学相辅而行,这两者的诸多事迹,都见之于孝武帝一朝。虽然成效不多,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
皇权的逐渐恢复,主要人物是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史籍所载,孝武帝是昏君,司马道子父子是乱臣,这些都是事实。但,在这些昏君、乱臣的某些行事中,却体现了门阀向皇权的转折。回复皇权,是回复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这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与评价门阀无关,也与评价人物无关。或者还可以说,正由于昏君乱臣当朝,本来是可能有所收获的恢复皇权的活动,才没有出现真正的成效,徒然成为一阵噪音,一场闹剧。
① 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其意义参见本书第二二五页。
① 《桓伊传》系此事于“孝武帝末年,嗜酒好内”之下,年代显误。《世说新 语·任诞》“王子猷出都”条注引《续晋阳秋》、《北堂书钞》卷一一○引 《语林》,叙及此事,均不谓在孝武末。《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曰: “是时昌明(案即孝武帝)年长,嗜酒好内”云云,可证《桓伊传》“末年”为“年长”之误。
② 磊砢,人才特出之意。《世说新语·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条:“其人磊砢而英多”。
① 王雅出东海郡望。
① 《晋书》卷七五《范宁传》作千余人。
① 东晋穆帝亦有讲《孝经》事,一在永和十二年二月,一在升平元年三月,时穆帝年十三、四年,主其事者为司徒会稽王司马昱,情况与孝武帝讲《孝 经》相似。
选自田余庆《东晋门阀》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