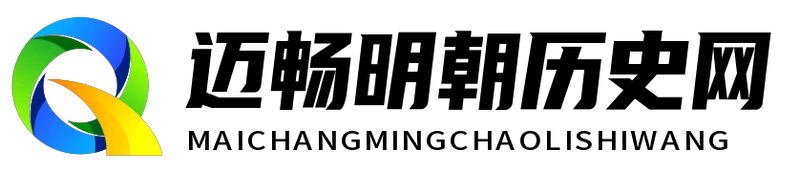在孔子去世之后那么多的著名儒者中,为什么从韩愈起的儒家主流学者偏偏挑选了一个在当时并不怎么特别起眼的孟子与作为“至圣”的孔子相提并论?
刘清平孟子何以亚圣

(作者:刘清平,复旦大学教授)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用“孔孟之道”作为“儒家”的代名词,因此也很少深入反思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重要问题:在孔子去世之后那么多的著名儒者中,为什么从韩愈起的儒家主流学者偏偏挑选了一个在当时并不怎么特别起眼的孟子与作为“至圣”的孔子相提并论,乃至最终在儒家的“道统”内赋予了他(而非颜子、有子、曾子、子思、荀子等人)以“亚圣”称号呢?本文试图围绕儒家的两大支柱理念——“孝”和“仁”,对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要想从核心价值的层面找寻儒家区别于中国乃至世界上任何文化的最独特之处,恐怕非“孝”和“仁”这两个概念莫属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尽管古往今来的儒者们曾经提出和阐发了大量都有儒家特色的概念(诸如“诚”、“敬”、“天理”、“良知”等等),但如果说去掉概念儒家仍然还有资格叫做儒家的话,一旦去掉了孝和仁之中的任何一个,儒家却再也不可能成其为儒家了。有鉴于此,我们要找到孟子何以成为亚圣的内在原因,自然也应当首先从作为儒家命根子的这两个支柱理念入手。
周公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但作为儒家的思想先驱,他已经论及了“孝”和“仁”的问题——虽然对二者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一方面,他只是在“予仁若考”(《尚书·金縢》)的自我评价中,单纯提到了“仁”这个字而没有加以阐发;另一方面,他又极大地强调了“孝”的重要意义,甚至还在“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的命题中,将其说成是人生在世的终极性“元善”。作为周公的真诚景仰者和儒家的真正创立者,孔子比周公前进了一大步,第一次从哲理高度深入探讨了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先来看“孝”。孔子一方面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的角度出发,颇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子女理应对父母尽孝的血亲理据,另一方面又直接继承周公将“孝”视为“元善”的看法,反复强调了它在道德生活中的源头意义:“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兴于仁”(《论语·泰伯》)。结果,以血亲之孝作为人伦道德的本根基础,便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大独具特色。事实上,在孔子的门生中,“其言似夫子”的有子便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明白把“孝”说成是“仁之本”,而据说撰录了《孝经》的曾子则进一步将其提升到“天下之大经”(《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的重要地位予以彰显。
尽管不是孔子的亲炙,孟子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点也不比有子和曾子逊色,毋宁说更富于创造性。首先,他把“爱亲敬兄”说成是人们生下来便拥有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从而无需诉诸“子生三年”的血亲事实,就充分彰显了孝悌规范的天经地义。其次,他不仅把仁义道德的实质内容统统归结为孝悌,主张“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而且还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在驳斥墨家夷子“二本”说的时候特别强调“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孟子·滕文公上》),明白将父母视为人生在世的唯一本根,并且从中得出了“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孟子·离娄上》)、“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著名结论,十分清晰地把“孝”说成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以致主张任何人一旦缺失了它,便不再具有作为“人”的道德资格了。也正是由于孟子的这种原创性首倡,在后来的主流儒家中,“孝弟”作为“元善”才不仅构成了“仁之本”,而且构成了“人之本”。所以,在涉及血亲情理精神的这些重大问题上,孟子可以说都的确是“发孔子所未发”,为儒家做出了独一无二的理论贡献。
二
再来看“仁”。与只是点到为止的周公不同,孔子不但在哲理高度上清晰地赋予它“爱人”的内涵,而且也更充分地肯定了它的价值意义,将它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以致儒家思想常常又以“仁学”著称。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他的下述命题之中——“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人们只要有志于“仁”,就不会在道德领域内做出任何“恶”的事情来了。事实上,只要在“不害人”的前提之上来理解“爱人”之“仁”,这个命题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信念确立为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普适性标准,明白主张:任何没有坑人害人、而是爱人助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任何没有爱人助人、而是坑人害人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恶”的,从而成就了人类道德意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历史进步。
不过,虽然也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泛爱众”(《论语·学而》)等见解,孔子毕竟还没有彰显“仁爱”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性意蕴,也没有清晰地指出“仁爱”对于“不害人”前提的依赖。同时,颜子虽然在践履仁德的方面十分突出,据说出自子思之手的《中庸》虽然强调了“仁者人也”,但他们也都缺乏足够扎实的理论建树。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儒者不是别人,又是孟子。
首先,孟子特别强调了“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从而无所不包地展示了仁爱针对每个人的群体性内涵。其次,他还明白主张“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从而通过“仁义一体”的途径,有效地弥补了孔子没能自觉指出“仁爱”以“不害人”为前提的理论缺失。尤其是他在独树一帜的“心性”理论中提出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等见解,更是将普遍性的仁爱直接建立在看到他人受到伤害便会生发出来的恻隐同情的基础之上。诚然,孟子在这些方面也从倡导“兼爱”和“公义”、反对“别相恶交相贼”、主张“杀一人谓之不义”的墨子那里汲取了一些思想资源;不过,这种借鉴并不足以抹煞他自己对于儒家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
进一步看,在孔子那里,“孝”与“仁”这两大支柱理念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反讽性的悖论了:一方面,他试图以血亲孝悌为基础实现泛爱众之仁;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命题,将孝悌凌驾于泛爱众之上,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不惜以放弃普遍性之仁为代价也要维系特殊性之孝,结果实质性地违反了他自己确立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
绝非偶然,在孔子之后,又是孟子最有原创性地展现了孝与仁之间的这种深度悖论,因为他不仅把血缘亲情说成是君子安身立命、实现仁爱的唯一本根,而且还把维系这个唯一的本根说成是人生在世的头等大事,明确主张“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更有甚者,他还通过赞美大舜圣王在“瞽瞍杀人”的情况下将其“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在弟弟无才缺德的情况下将其“封之有庳”(《孟子·万章上》)的举动,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为了维系本根至上的慈孝友悌,不惜否定恻隐仁爱的伦理规范,乃至从事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举动,结果同样实质性地违反了孔子确立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
综上所述,孟子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孝”的特殊性维度,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强调了“仁”的普遍性维度,结果不仅比孔子更充分地展示了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而且也比孔子更充分地彰显了两者在儒家架构内所陷入的深度悖论。
三
如果说孟子在孝和仁及其悖论性关系的问题上都大大发展了孔子,那么,其中主要又是哪种因素直接导致他被后世主流儒者纳入道统、奉为亚圣的呢?细究起来,应该说是孟子在普遍性仁义观念方面做出的无法替代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本来,在孟子之前,不但周公和孔子,而且有子、曾子、子思等人,都已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肯定了血亲孝悌本根至上的终极地位。因此,孟子虽然在彰显其唯一性方面确有创新,但毕竟还难以说成是鹤立鸡群。相比之下,只有在普遍性仁义的问题上,他才真正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实现了理论上的原创性突破,不仅实质性地超越了偏重亲身践履、缺乏观念建树的颜子,不仅实质性地超越了重视孝超过仁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还实质性地超越了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本人,因此属于最明显最深刻的“发孔子所未发”。同时,在孟子之后,虽然荀子和董仲舒也因为大力推崇“礼义”和“三纲”的缘故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却又流露出强调“忠孝”胜于“仁义”的片面性,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用“忠孝不能两全”的伦理悖论替代和遮蔽了“仁孝不能两全”的伦理悖论。从这个角度看,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虽然献身儒学的人士难以数计,却只有孟子一人真正原创性地发展了孔子的“爱人”之“仁”观念,不但将其推扩到“无不爱”的普遍性之端,而且还将其与“不害人”之“义”内在地结合起来。
唐代韩愈第一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在《原道》中描述儒家“道统”的时候他曾明白指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不但没有提到与孔子关系更紧密、同时身为孟子师长辈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也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贬抑了当时颇有名气的荀子、扬雄等人。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更是明白点出了孟子超越他人的“精详”之处:“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所以,毫不奇怪,他在《原道》中最强调的两句话便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众所周知,韩愈撰写《原道》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排佛抑老”的途径维系传统儒家的正统地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从孔子那里也很难找到像“恻隐”观念和“心性”理论这样足以与佛禅倡导的普遍性“慈悲为怀”、“直指人心”见解相抗衡的思想资源,他才会公然撇开这一千多年间的众多显赫儒者于不顾,沙里淘金地单单挑出了孟子这位将仁义原则推扩到普遍性之端的儒者,把他说成是孔子思想的唯一人——所谓“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
尽管宋明儒家对于韩愈说的“博爱之谓仁”也有一些微词,但由于同样承担着“排佛抑老”的历史使命,他们也只能是别无选择地照着他首倡的“道统”讲,在孔子之后首先从孟子那里汲取种种精神养料和理论资源,凭借彰显“仁理”或“仁心”的“理学”、“心学”,来对抗佛教“慈悲”观念以及道家“齐物”观念向儒家提出的严峻挑战。对此他们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事实上,朱熹在选编《四书》的时候,之所以独具慧眼地在专门记录“子曰”的《论语》、高度提纲挈领的《大学》和富于哲理意味的《中庸》之外又挑中了《孟子》一书,却毫不手软地把先秦儒家论著(包括大名鼎鼎的《孝经》)统统弃之一旁,主要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或许是下面的事实:尽管《四书》中也收录了据说分别为曾子和子思所撰的《大学》和《中庸》,尽管他俩都是无可争议的孟子师长,并且与孔子的关系应该说更直接更亲密,但两千年儒家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亚圣”桂冠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最终还是以“舍我其谁”的方式落到了只能算作孔子远房的孟子头上。无需废话,单凭《孟子》一书的篇幅最长,肯定不足以解释这个奇异的现象;只有诉诸它包含的远比《大学》和《中庸》更富于原创性的思想观念,我们才能找到个中隐藏的玄妙天机。
从这个角度看,孟子之所以能在从先秦直到唐代的万千儒者中异军突起、一枝独秀,成为儒家思想史上唯一有资格能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人物,荣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亚圣”宝座,绝非只是出于偶然地由于韩愈等人的一时兴起,毋宁说是儒家发展脉络的逻辑使然。换言之,即便韩愈等人当时没有把孟子纳入“道统”,后世肯定也会有其他儒者出于儒家发展脉络的内在需要,不惜舍弃孔子的众多亲炙、再传门生乃至血脉嫡孙,单单挑出当时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的孟子,作为绵延孔子思想的头号传人。原因很简单:只有孟子才以后世儒者绕不过去的原创性方式,继承发展了孔子首倡的普遍仁义观念。
四
尽管孟子凭借他在普遍仁义观念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成为儒家当之无愧的“亚圣”,但如上所述,他也没有因此消解、相反还进一步加深了仁与孝在儒家架构内陷入的内在悖论。只是强调孟子的普遍仁义观念在“排佛抑老”方面的理论效应的韩愈和宋明儒者,当然就更不可能跳出这种悖论性架构而否定传统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了。结果,对于儒家来说,仁与孝这两大支柱理念的张力冲突也因此构成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根本问题,以致历史上的所有儒者都没法绕开它们之间的深度悖论——就像他们没法绕开孟子做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那样。
从两千多年的儒家发展史看,不仅察觉到、而且试图克服这个悖论的第一位儒者,当推现代新儒家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他在“衰年定论”中反复指出:虽然孔子五十岁后转而“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但其早年却积极倡导“以宗法思想为主干”、偏重“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并且极大地影响到了孟子荀子以及宋明儒学(见《原儒上卷·原外王第三》、《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他还一反以往主流儒家的通行定位,别出心裁地认为孟子比荀子更狭隘更固蔽:“孟子、荀卿同是坚守小康之壁垒,与大道学说之主旨根本无可相容。孟子最顽固,宗法思想狭隘一团。”(《乾坤衍·辨伪》)而他为此给出的论证恰恰是:“孟氏似未免为宗法社会之道德训条所拘束,守其义而莫能推,则家庭私恩过重而泛爱众之普感易受阻遏”(《论六经》);“孟子主张以孝治天下,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曾、孟之孝治思想……其贼仁不已甚乎!”(《原儒上卷·原学统第二》)显而易见,在这些论述中,熊十力已经敏锐地揭示了以普遍仁义为主旨的“大同之道”与以血亲孝治为主旨的“小康礼教”之间的张力冲突。
当然,熊十力对孔孟的批评也有某些偏颇之处。先就孔子来看,便不存在早年坚持小康礼教、晚年倡导大同之道的历时性二元对立;毋宁说,他早年就积极推崇“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念,晚年也没有放弃“君臣父子”的宗法思想,两者在其理论架构中始终保持着悖论性的关系。再就孟子而言,虽然他一方面的确在“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命题中以极固蔽的形式呈现出小康礼教的“贼仁”倾向,但另一方面也以极开放的形式将“仁者无不爱”的大同理念发展到极致,从而不仅比很少谈到仁爱问题的荀子更包容,而且也比没有论及“恻隐”、“不忍人之心”的孔子更深刻,并且恰恰由于这一缘故才得以成为儒家的“亚圣”。不过,尽管存在种种缺陷,熊十力试图通过这些批评找到一条消解儒家仁孝悖论的途径,还是充分体现了他作为20世纪最富于原创性和批判性的儒家大师的理论特色,同时也因此真正奠定了他在现代儒家思想史上同样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地位。
从这里看,我们能从孟子成为儒家“亚圣”的根本原因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迪是:要想在当前现代化、全球化的氛围中重新激发儒家的生命活力,我们就应当像现代新儒学的创始人熊十力那样,一方面深刻批判儒家鼓吹“天下为家”的小康礼教,彻底打碎忠孝至上的特殊主义架构,另一方面积极弘扬儒家主张“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赋予普遍仁义以压倒一切的终极意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像墨家的“兼爱”和“公义”观念、佛教的“慈悲”和“平等”观念一样,孔孟的“仁义”观念在“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内涵上与来自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观念也是内在一致的,充分体现了“尊重每个人应得权益”的交叠共识,凝聚着人类在道德领域尤其是正义维度上的终极底线。熊十力在《乾坤衍·辨伪》中的一句“衰年定论”,便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天下人一律平等,各得自由,互相和爱,互相扶助,是为公。”有鉴于此,如果说正是孟子对于孔子仁爱观念的原创性发展才使他能够在儒家“道统”中享有“亚圣”地位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也只有在“后儒家”的架构中高扬孔孟的普遍仁义观念,才能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确立起中国儒家作为“仁学”的重要地位。
人学研究网·千秋人物栏目责编:莫如朴
标签: 明朝历史记载 、 严嵩和海瑞什么关系 、 元代野史 、 中国历史朝代演变图 、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石悦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