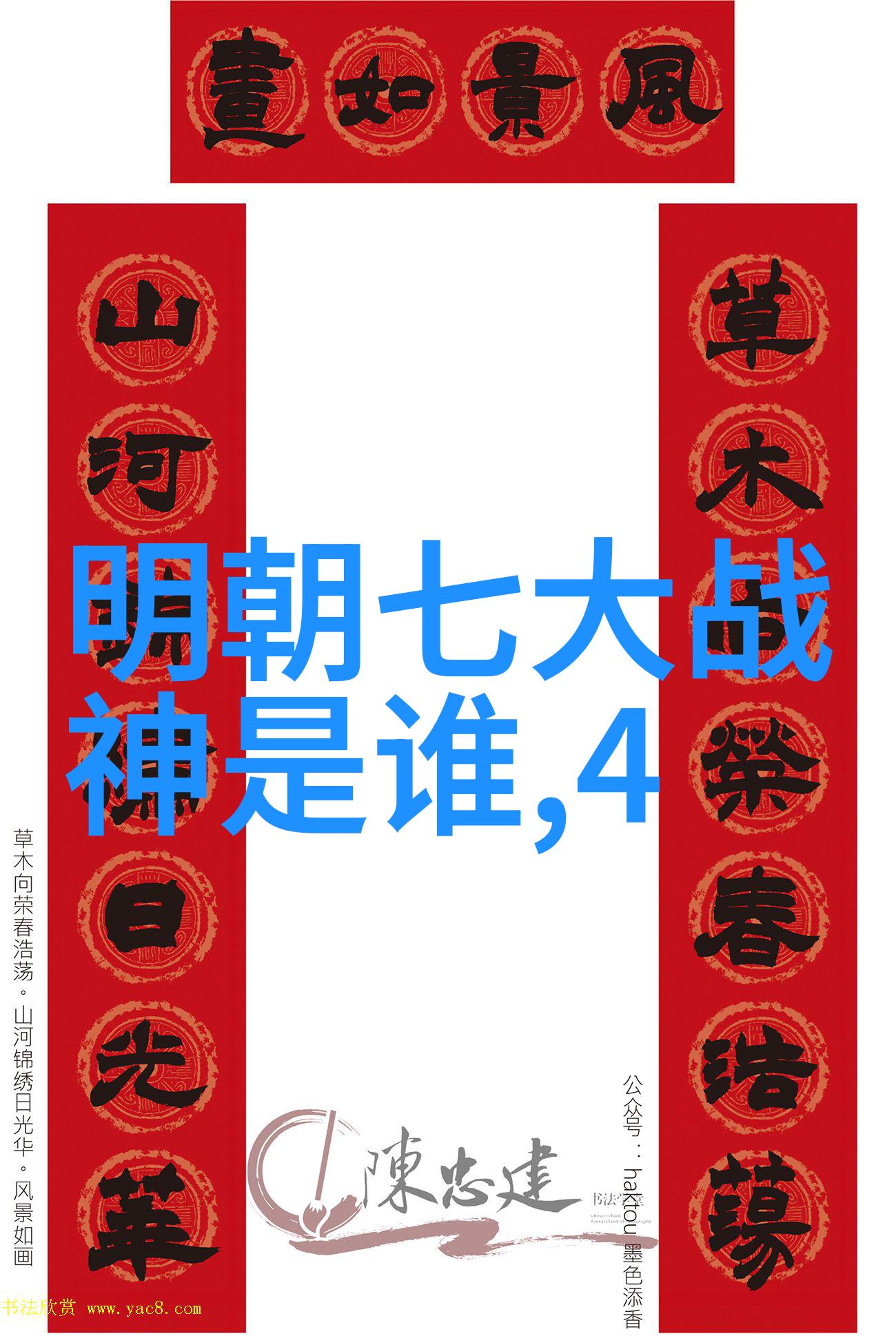我看到了一个广告,而且还有一张图片,它显示了一个小巧的楼,是外城西南角楼,据说1952年已经被拆除了,它只有12个箭孔,不是很大的一个楼。这张图片真是美妙极了。当我乘坐列车即将进入北京站的时候,我总是能从左侧窗户看到城墙上的一座雄伟的曲尺形箭楼。这座楼是内外城八个角楼中唯一存留至今的内城东南角楼。如果一百多年前我登上这座角楼向城外看,就能看到宽阔的护城河和通惠河,并且还能看到东便门漕运码头的繁忙景象,这里是整个北京城市水系的出口。向城内望去,依然可以看到水,一条弯曲的小河将几个清澈的水池串联起来,像一条翡翠的项链,北京人称之为“泡子河”。
内城东南角楼是唯一幸存的角楼
说起角楼,人们总会想起故宫城墙那四座“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角楼。它的结构奇特,和谐美观,是中国古建筑的极品代表作之一。其实,明清时代的北京内外城角楼还有八座不同的造型。但是,唯一幸存至今的是内城东南角楼。至于其他的七座角楼,早在清朝末年时就已经拆除,今天只留下了它们的名字和一些记录。我知道,这些角楼不仅有装饰作用,还设有军队驻扎,以备随时防御敌人的攻击,因此都被设计成箭楼。其中,紫禁城正面的内城西南、东南两座角楼规模最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剩下的七座角楼或在清末的雷电和战火中毁灭,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市建设中被拆除。
现在还存留下来的是内城东南角楼,建于明朝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那个时候,永乐皇帝在修建北京城时,由于资金、物资和时间紧缺,“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直到正统元年,他下令修筑九门城楼,次年正月施工。明《英宗实录》记载说:“四年四月丙午,修造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城四隅立角楼。”这些文字清楚地记载了北京内城有角楼的历史。而明嘉靖年修筑外城后,内城南部的两座角楼就被括在北京城墙之内。历代修建的角楼经过多次修葺和重建,例如乾隆皇帝曾大规模对北京所有城楼进行修缮和彩绘。这座角楼建在城墙的方形台座之上,呈现曲尺形状,高29米(其中台座高12米),底边长39.45米,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它的结构非常坚固,易于守卫和难以攻击。在十字交汇处,有两条大脊,呈现出灰筒瓦绿色剪边的风格,同时配有绿琉璃饰兽头的列脊。在楼的外侧,向东、向南、向西、向北各有箭窗,共计144个,是国内现存箭孔最多、方向最多的箭楼之一。楼体内侧也呈现转角房的样子,有两个门。楼内共立有20根楠木柱,楼板分为三层,以配合上面三层的箭孔。
1981年至1983年,政府拨款重修了角楼,遵循着不改变原状的修缮原则,恢复了年代久远的历史痕迹。我们对角楼进行修缮后,重新恢复了其旧貌,并设立了保管所,筹备展览,并且现已对社会开放供游览。多年来,不少人称这个城楼为“东便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东便门实际上建在角楼以东约200米处的外城上,已于上世纪50年代拆除。
我曾到过大通桥畔,这里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漕运码头之一。这两张照片是摄于东便门外的漕运码头,据说是一位名叫查尔德的德国摄影师拍摄的,具体年代可能是1875~1878年,距现在已过去一个多世纪。通过这两张照片,可以看到北国水乡的美丽画卷,如果不是内城东南角楼和巨大的北京城墙,我们还以为是苏州水城呢。在古代,漕运是元、明、清三代最重要的官办经济活动,也是将富庶的南方田赋集中到首都的一种重要方式。明清两代,南方的漕船北上,或走海路,或走运河,经过通州张家湾到达北京。我曾经到过张家湾,这里是漕运的主要中转站之一,漕船可以在这里卸下漕粮并继续向北航行,也可以沿着通惠河西行,到达东便门大通桥码头,甚至直达朝阳门码头。在元、明和清前期,北运河和通惠河是首都的生命线。上面照片中央的美丽三孔石桥是大通桥,又称为“东便门桥”,建于明嘉靖年间,清康熙时期重建。桥边的码头在明清两代是漕运的重要码头,也是漕粮从东便门进入城市的通道。大通桥下有一座闸门,俗称“头闸”,建于清康熙年间,其作用是控制通惠河上游的水位。据说小说《红楼梦》中的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林黛玉就是在大通桥码头上岸的。
码头上停泊着十余艘平底大木船,这些船的大小和形状几乎完全相同,应该是政府的“剥船”(或称“驳船”)。太平天国之后,大运河淤塞了,不能再行驶漕船,遂开始打造可在沿海运作的“沙船”、“夹板船”,或者租用招商局轮船走海路,从天津直达海河。然后换装能够在内河行驶的“剥船”。我了解到,我们可以经过北运河和通惠河进入北京,这种船运方式被称为“剥运”,也就是“由大船换小船”的意思。清末时,“剥船”是粮仓管辖和使用的,各个粮仓都要按照规定形制根据邻近河道的宽度和吃水情况来打造剥船。在通惠河上航行的剥船长六丈、宽一丈二尺,可以容纳一百多石的粮食。它们可以单独行驶,也可以串成一条线,由拖船拖带航行。照片中带篷的木船很可能就是拖船,拖船可以由漕夫用竹槁撑行,但如果遇到旱季的浅水区或者雨季的急流,就需要纤夫了。 纤夫和漕夫必须在浅滩的河道中拖船几条几十吨的剥船逆流行驶,他们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自道光五年以后,部分漕粮折合银两,随着田赋一起上缴,这减少了运输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全部的粮食运输都改用机动船和铁路列车运输。这样,跨越了元、明、清三朝,延续了500多年的漕运终于逐渐从历史中淡出。
照片左侧的尖顶建筑是官府粮仓,在清代叫做“储济仓”,可能是个临时转运站,那些“剥船”应该归储济仓管辖。我发现,上面照片中远处可以看到外城东北角楼,下面照片则是内城东南角楼。两张照片都没有将东便门本身拍进画面,但我知道东便门是外城的城门,规模很小,还有一个不大的瓮城,正对着大通桥。
大通桥和东便门的水系是元明清三代城市水网的枢纽,它东联通惠河,向北是西护城河,向南是外城护城河,正西是前三门护城河。高梁河水从玉泉山到西直门后分成三路,到东便门后全部流入通惠河。北京城的生活污水和雨季的洪水很大一部分都通过这里进入通惠河、北运河,最终流入海洋。
由于人口激增和城市建设,北京古城墙和城市水网在几十年内被彻底改变了。特别是从1965年开始,地铁一号线的建设导致城墙被拆除,护城河河道被占用。东便门大通桥是与万宁桥、高梁桥和天桥齐名的,但在1966年时也被拆除了。很遗憾,东便门大通桥在上世纪被拆除了,但我很庆幸前三门城墙残留下来的部分被开辟成了一个公园,通惠河也经过整治,在不远处倒映着城墙的角楼,试图让我们回忆起东便门从前的美景。
我了解到,泡子河曾是元代通惠河的一小段故道。上面的两张照片非常珍贵,拍摄于1913年。虽然泡子河的水面已经比明清时期缩小了不少,但我们仍然能够想象那时的美景。通过照片,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曾经是北京城非常宁静的去处。
在元代,泡子河是通惠河在城外的一小段故道。明朝迁都北京后,将元大都南城墙南移二里重新挖掘了护城河。在建城过程中,暂时使用了这一段河道,引出六海洪水。明内城建成后,这段河道就成了内城东南角的一段“盲肠”。由于这里比较低洼,沿河有几个积水的水洼,小的有十几亩,最大的近百亩。北方人称之为“泡子”,因此这段河道也被称为“泡子河”。我发现从清代乾隆年的地图上看,崇文门以东的城墙下有个水关,使泡子河与前三门护城河连成一条泄洪通道,成为了北京内城的一条水道。据《燕都游览志》记载,这里“前有长溪,后有广淀。高堞环其东,天台峙其北”。泡子河有两条河道:一条起自贡院以东,经古天象台向南流入“泡子”;另一条是通惠河的故道,起点是船板胡同的西口,沿着内城前三门的北城墙,向东流入泡子河。至于泡子河的水源,《帝京景物略》说:“洼然一水,泡子河也。积潦耳……” 这表明它是由于地势低洼,积雨水而形成的。
在明清两朝,泡子河是远离车马喧嚣的好去处,“两岸多高槐垂柳,空水澄鲜,林木明秀,不仅在秋冬时分,任何时节都难以遗忘。” 它是北京城内環境優美,景色宜人的好去处,吸引了不少文人学士、达官显贵来此修建宅邸和私家园林。几个寺庙也利用泡子河的灵气,建在河边,如供奉吕洞宾的吕公堂(又称吕仙祠),还有慈云寺等。泡子河北部的贡院,是明清两朝的科举乡试和会试的地方。我了解到这里曾是重要的殿堂,许多帝王都曾到此处视察过。每年春秋两季赶考的各地学生都会来到吕公堂、慈云寺祈求圆梦,据说效果不错,因此庙会和香火十分兴旺。
据红学家周汝昌考证,曹雪芹可能出生于泡子河边的曹家宅邸“芷园”。清朝初期,曹家从北方迁来,原隶属于正白旗,后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被任命为江宁织造,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掌大悬香阁,文光射斗魁。”诗的注解是:“芷园小阁,邻试院(贡院),寓公多利。”
在那个时代,泡子河水上有船,岸边有人垂钓,夏季还有很多人在河里游泳、洗澡。直到上世纪中叶,这里还有“船板胡同”、“鲤鱼胡同”和“钓饵胡同”。《帝京景物略》记录了明朝末年的景象:“在七月十五,各庙会聚,水灯连夜,其中最出名的是水关(积水潭)和泡子河……”也就是说,在明朝时期,阴历七月十五,泡子河的水面上是放河灯的好去处。
清朝灭亡后,这里逐渐沦为贫困区域。大量人口涌入,修建了许多简陋的房屋和建筑。
我了解到,这里的生活污水和垃圾,使几个泡子成为死水;在日本侵华时期,又有一个叫“启明门”(现在的建国门)的区域造成了北部水源的断绝。新搬来这里的居民们都在这里填河造地建房,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泡子河已变成一个臭水沟。
20世纪50年代末,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让这里变成一片工地,新北京站及其东面的车辆段,占据了泡子河的大部分流域面积。现在的内城东南角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社区,看不到一点水乡的景色了。只有少数一些地名,如“泡子河东巷、西巷”、“泡子河社区”能让人回忆起这里曾经有过一条美丽的小河。
盔甲厂,明清两代的“军工重地”
现在的北京站东边,泡子河东巷里,还有一条“盔甲厂胡同”,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里曾经生产过官兵使用的盔甲。
在明代,工部军器局曾经在王恭厂和泡子河边设立厂房,生产军用盔甲、火炮、弓箭、弹药等军需品,各个厂房都有相应的官衔. 例如,泡子河岸边的这家厂子称为“圆明园穿铁局”。到了清朝时期,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建和改进,生产的盔甲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整个厂区保留了许多古代的建筑和地下工程的遗址,这些老厂房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古建筑群体和文化街区,吸引了很多游客。我了解到,“掌厂太监”这个称号其实是国家设立各种军需工厂时的官名。在明清两代,人们一般会在城角地区建造生产、储存兵器和火药等的厂房,比如东北角的“火药局”、西北角(在雍和宫以东)的“炮局”。
城角离城门较远,两面是坚固的城墙,易于防守;而且离居民稠密区远,如果发生燃烧、爆炸等事故,就可以减少周围居民的损失。盔甲厂建在泡子河边,不仅可以及时取水和救火,而且造成事故时也可减少对周围的影响。尽管如此,工厂还是难免经历过两次大爆炸,分别是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和崇祯七年(1634年)。特别是崇祯七年九月初七的那次爆炸,石碾撕裂,火药四散,远远抛落于泡子河城墙下。这次爆炸和随后引发的大火摧毁了许多明代建立的私家园林,例如傅家东、西园,张家园,房家园,杨家园等。
清代时,盔甲厂已经改为存放废弃炮枪的仓库。危险自然得以解除,于是胡同也多了起来。很多胡同都形成于清代,而盔甲厂胡同就是其中之一。盔甲厂是与许多历史事件紧密相关的街区之一。我提到盔甲厂,就不得不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轰动中外的著名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以及它的作者埃德加·。他在1933年到1937年期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和他的夫人海伦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盔甲厂13号院内,不远离位于南城根的燕大教职工宿舍——“燕京大学花园”。
在1936年下半年,他来到陕甘宁苏区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回到北平以后,他就在13号院中的一个小屋内,几乎日夜不停地整理采访记录和赶写书稿,怀着对、朱德、周恩来等红军以及前线将士的敬仰,使出了浑身解数。1937年10月,英文本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1938年7月,它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发行。他用丰富而详实的材料、幽默而生动的文笔,率先向欧洲、美国人民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抗战的艰苦历程,使得这个充满传奇的历史时期深深地印在大家的记忆中。
今天,盔甲厂胡同和13号院等地名仍沿用至今,为大家展现了这片曾经辉煌的历史景象,让人们了解到过去这里曾经发生的许多充满传奇的历史事件。我所居住的盔甲厂13号院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这里曾经有着震惊中外、举世罕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人类史上的奇迹不仅在中国大地上,也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扬。而我住的这个院子里住着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邓颖超同志。不少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专程来到这里感受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在中国的国统区和敌占区,《西行漫记》第一次让百姓知道,在西北的黄土窑洞里,那支被称为“”的队伍才是未来照亮中国的红星。这个书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仅仅几周的时间就销售了5版、10万册以上,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意义的著作”。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很多抗日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冲破重重阻拦,投奔到圣地延安。 1938年夏天,我在盔甲厂13号院,接待了来自山西福寿岭疗养院的“李知凡太太”。在日伪特务的眼皮底下,我护送她出北平再由爱泼斯坦护送到天津、烟台。而这位“李知凡太太”就是邓颖超同志,成为了我与革命战斗的开始。在此之前,还在这个院子内,我也掩护过多名受的进步学生领袖。 据老住户回忆,当年的盔甲厂13号院是一个集聚了很多抗日英雄和进步人士的地方。这里被誉为都市地下工作者的大本营。这是我家曾经的所在地,这里有着那段充满传奇的历史。盔甲厂胡同6号院,曾经是一个花园式的院落,满是绿树、翠竹和假山。这个地方承载了不少历史,而我住在这里也有着很多回忆。 1965年,盔甲厂改为“盔甲厂胡同”,13号院也被改为6号院。如今这里是一家“中安宾馆”,不同于以前的花园式院落,更像是一个商业设施。但是每当我从宾馆门口经过时,眼前的景象总能勾起我对那个花园式院落的回忆。每一次路过这里,心中总会涌起那份难以言表的情感,仿佛看到了过去我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经过岁月的更迭,这个地方或许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模样,但是它所承载的历史和记忆,却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让我铭记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