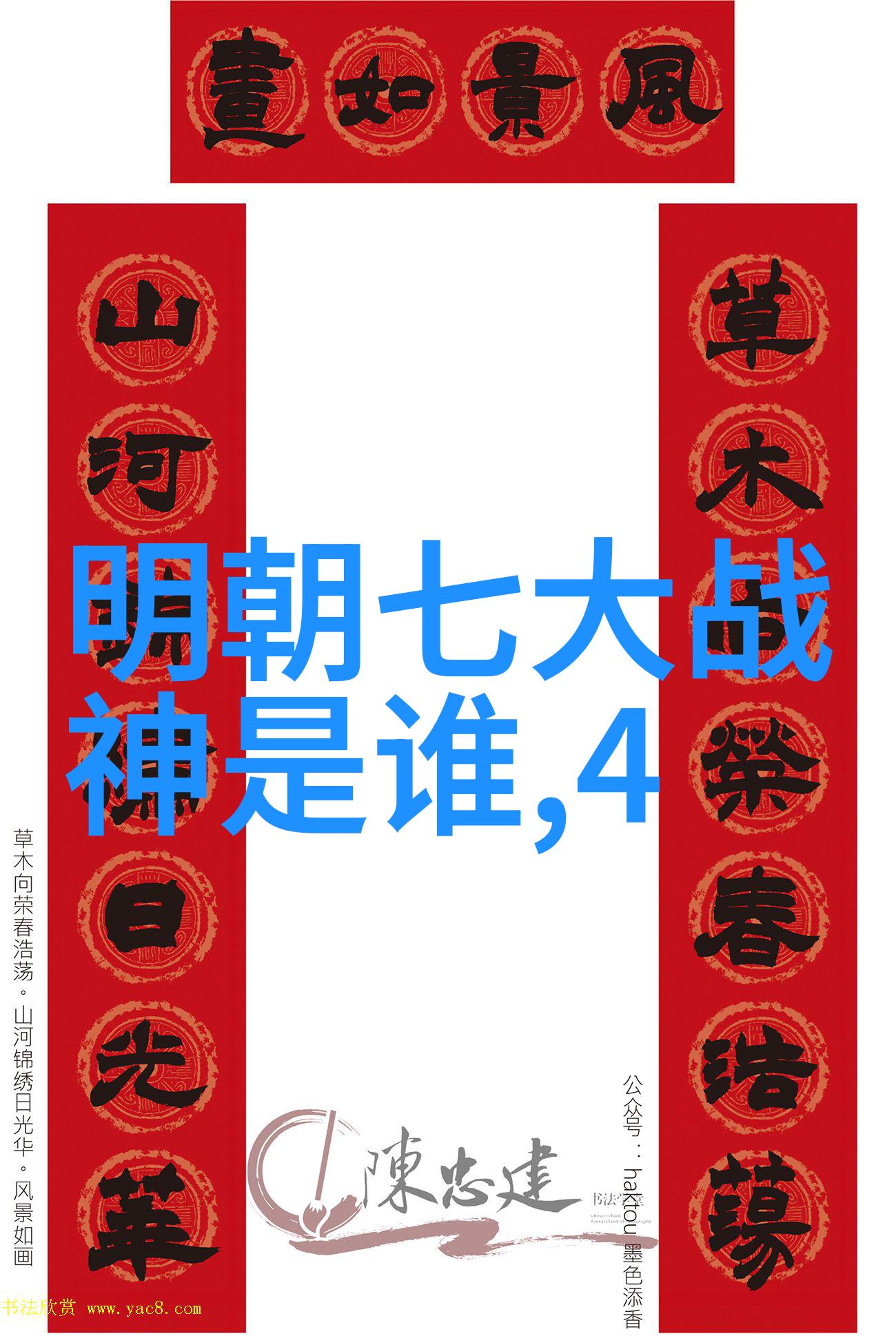我是一名欧洲传教士,几经艰辛,终于来到中国。我的目的是要在这里传教,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但是我发现,中国和我们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都不一样。我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好地进行传教工作。虽然有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依然会坚持下去,相信天主的旨意。我是一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工作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和利玛窦一样,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学术叩门而入,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争取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用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来传教。这样做,我们不仅成功地进入了中国,而且还进入了宫廷,得到了崇祯、顺治、康熙等明清两代皇帝的器重和礼遇。我们和中国学者密切交往,打开了天主教传播的大门,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汤若望就是我们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在德国科隆出生,原名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在来到中国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天文、数学都有研究。他于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进入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7年。作为一名入华耶稣会士,我在明朝末年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带到了中国。徐光启等士大夫对此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采用西洋新法推算,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我和其他传教士一起协助修订历法。崇祯皇帝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在北京宣武门内开设了历局,我和邓玉函、龙华民等人进入历局工作。不幸的是,邓玉函去世了。在徐光启的推荐下,我离开陕西,来到北京,进入历局任职。我和徐光启、罗雅谷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天文学著作,制造天文仪器,修订历书。不久,明朝灭亡,崇祯皇帝去世,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我决定留在北京,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着生命危险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单介绍。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作为传教士和历学家汤若望,我知道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有密切关系。因此,清朝大学士范文程非常重视这一点。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显示新朝的崛起。通过范文程的推荐,我得以进入清朝宫廷,修订历法。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了我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我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还任命我执掌钦天监,成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从此,我步入了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推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事业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和对皇帝的忠心,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了执掌钦天监之外,我还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重要职务。为我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我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的一位倍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年轻的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我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爷爷。),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我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我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使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我竭诚为顺治帝效力,我的目的是为了争取顺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顺治帝对教会产生好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一条广阔的道路。因为我的不懈努力,我被加封了大夫等品衔,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我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谕旨和发布御制天主堂碑文的时候,我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向顺治帝传教布道。我付出的苦心并非毫无效果。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我的影响。而且顺治帝对我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我所代表的西教西学表现出明显的好感。顺治十年(1653),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奖我。顺治十四年(1657),钦赐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匾额“通玄佳境”。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我的影响又极为有限。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汉文化作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以及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必须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等一系列原因,决定了顺治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文化。就在我受宠最隆之时,顺治帝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赐我“通玄教师”的谕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顺治帝就说明了他对我加官进级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对天主教的态度。在谕旨中,顺治帝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了我的治历之功,明确指出:“我承天眷,定鼎之初,谘询你的名字,为我修大清时宪历,直到成功,可谓勤劳。你又能洁身自好,尽心尽力,统领群官,可谓忠诚。”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可以看出,顺治帝之所以对我不吝封赏,主要是因为我在明清易代之时,修订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因此,顺治帝要对我予以重用,加官进级,以表彰我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至于天主教,顺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而天主教是西洋宗教,他不懂其信仰。顺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我已经认识汤若望多年,他能够信仰自己的宗教,建造祠堂,认真维护清洁,始终坚持,认真而诚实,值得尊敬。臣子怀着这种心思来侍奉君主,还未有不尊敬他的。”这表明顺治帝认为我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员以我为榜样,忠诚地尽职尽责。